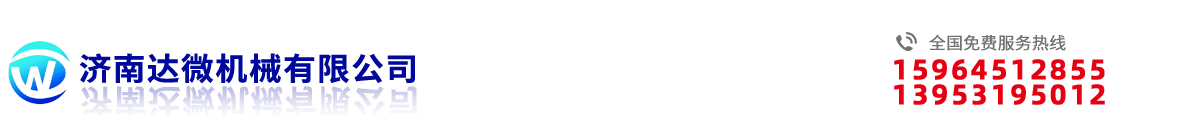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̽��
�l(f��)���r(sh��)�g��2014-11-22 11:31
ժ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ɣ��ɷ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(c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߉ƫ�H��ֻ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Ŝ�(zh��n)�_�ذ���ס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ăr(ji��)ֵ�cʹ�����ɞ��ͨ����Փ�c����Փ֮�g�Ę������@Ҳ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鱾λ������О�ּ?x��)w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
�P(gu��n)�I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Ļ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չ�_�^���ճ־õĠ�(zh��ng)Փ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_���f����19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픷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أ�Schubart��1739��179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(n��i)�ݶ�����ʽ���ǛQ������Ե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ԊW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ߝh˹���ˣ�EduardHanslick��1825��190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W(xu��)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c��(n��i)�ݵą^(q��)�֣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ji��)ֵ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Q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(n��i)�ݾ��ǘ��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(d��ng)��ʽ”��[1]һ�ٶ����^ȥ�����@��(ch��ng)�Բ�����֮��?q��ng)��Ġ?zh��ng)Փ�mȻ�ѳ��矟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ӑՓ��Ԓ�}��Ȼ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@Щ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Ҫ�ؾ�¶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ѿ���c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˂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̽ӑ��Ȼ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Ҳ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˵��Ļ����Ե���Ҫ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oՓ���Ї��ŵ䘷Փ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w�ı��_(d��)��
1.�|���Ļ��¹ŵ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˵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ɫ���v�[�Ї��Ŵ�˼��ʷ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Ї��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^��һ��؞֮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ӛ�d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�“�d��Ԋ�����ڶY�����ژ�”Ҳ�V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“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u(y��)�o�u(y��)”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ص��q�Cɫ������ֵ��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@Ƭ�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
���ܵ���ҕ��ԭ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f�ס��f��ī�ȹŵ�˼��ҵ���Փ���H�H�ǡ��Yӛ•��ӛ���о����S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r(sh��)�Ȅ�(sh��)���ܵď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磬“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”��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��c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֮��Թ��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c��ͨ��”�����۵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ε��A(y��)ʾ��Ч��
�Ї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“��”��һֱ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ƶȽ��O(sh��)֮���ĵ�“�Y”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ӛ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@�ӵ�ӛ�d��“���c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Y�c���ͬ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ͣ��ʰ��ﲻʧ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жY�����Ąt�й���”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^“���ߞ�ͬ���Y�ߞ鮐��ͬ�t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t�ྴ”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Ї��˵�ҕ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Ҫ���ڞ���Ⱥ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ṩ���㡣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Ч���@һ�c(di��n)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˹ŵ䘷Փ�Ļ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
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A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ֵ��ע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κ�x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o����Փ”�����@ƪͬ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ĝh�ԁ��Ĺٷ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“֮�c������Ϳ��܉�����ཛ(j��ng)��”���Ķ�Ԫ�f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ֻ��“��Ȼ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ĆΏ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c�f(xi��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֮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(n��i)�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^���A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�һ�N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ď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ģ�“����غϵ£��f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ɫ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Ҳ��”[2]����˞�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S���У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ϕ�(hu��)��Ɍ�(du��)�䪚(d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Ե��ַ����ڴ˻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һ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“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ژ�”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һ�N֔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БB(t��i)�ȣ�“��֮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Ğ������ʟo֮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ĸ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C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࿂�^֮����Ȼ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ڴ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ʹ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֪��֮���ɷ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֮���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[2]�@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äĿ�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x��
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ܵď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c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“�o����Փ”�ď��P(y��ng)����ͬ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Ї��ŵ䘷Փ�еăɹ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҂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⣬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γ����Ԍ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Ԟ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2.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�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Ƶ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c����Փ֮�g�ǻ���һ���J(r��n)�飬�Խ������Ҙ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Ѓɴ�M�ɲ��֣������Z�Ԟ�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L(f��ng)�}�����ڞ�һ����ͬ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“�o��֮��”�������sʼ�K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Ĵ��ڡ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ܸа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ڱ��ڽ��c���Γ�(j��)�鼺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1947����_�R�̻�ͨ�I��Ү�d�����ա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棺�ڽ̕�(hu��)���(d��ng)�У�“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ȿ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ҵ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y��ng)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ȥ�Ďׂ�(g��)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ٝ���ں���һ��”��[3]�ɴ�Ҳ���܉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“�ڂ��y(t��ng)�ڽ�ˇ�g(sh��)�ķՇ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ҿ��Dz��ò�ʧȥ�Լ��Ă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Ա�ʹ�Լ���ȫ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F(xi��n)�Ĺ�����”[4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һ�εǻ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]����һ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ȡ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Ĺ��ߡ��ɴ����ó����½Y(ji��)Փ�����@��ͻ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L��̎������Փ�Ļ\��֮����
ֱ��19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ԝh˹���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Ҳ��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(d��)�ص�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ژ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ąf(xi��)�{(di��o)�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ϡ��w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———�@Щ�|�������ɵ���ʽ�ʬF(xi��n)���҂�ֱ�^�����`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ʹ�҂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[1]�@һ�f������ՓĿ��(bi��o)���г������c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ص�(li��n)ϵ��ֻע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ࡢ���c���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(bi��o)�eһ�N�¸߶���ؓ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Ƅ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ΑB(t��i)�о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w��λ���湦���ɛ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Ұ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؞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пչ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
��֮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c�ڽ̙�(qu��n)���ĊA�p�����棬�Ї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c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Ե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?c��)ڲ�ͬ�r(sh��)�g�ﶼ���A �^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ĺ�����ʼ�K�����Ԕ[Ó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ΑB(t��i)Ԓ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DZ�Ȼ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^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Փ�c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ʷ�ϵ��p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üȱ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µ�ֱ�ӽY(ji��)���ǣ��҂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ʼ�K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ڹP�߿�����Ҫ��Q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회����}߀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ҕ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r(ji��)ֵ֮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̽ӑ���W(xu��)ʷ�ϵ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߀��“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Ć��}��
1.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
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ʼ�K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z���Ļ�Ŀ�̖(h��o)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Լ��Ą�(chu��ng)��ʹ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Ҷ����^��Ƶı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}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÷�~���@���f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еĺ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”��“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���ʾ�҂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l���҂��挦(du��)ʲô���ڰͺ���Ī���ء��沮�ص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���҂��Լ��c�o��֮�g��ͨ��”��[5]�@��ij�N�̶������A(y��)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 �c�x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Ҳ��Զ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ϣ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p�Č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�Ҳ�o�r(sh��)�o�̲�ӡ�C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�˿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̖(h��o)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�ӹ���ɵ���Փ�ϵĺϷ���———ͨ�^��(du��)“����”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}Ŀ�ď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ƺ��ь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Ŀ��(bi��o)Ш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ѿp�����҂��I(l��ng)��(hu��)ˇ�g(sh��)�ăr(ji��)ֵ�ṩ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ĽǶ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ϵĺϷ��Բ�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`�ϵĺ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ʷ�Č�(sh��)�`ǡǡ���V�҂�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Ƕ��ǵ�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߉©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^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^�ں����}Ŀ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�ڿ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ʹˇ�g(sh��)�ݳ���(y��ng)�е�߅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ʹˇ�g(sh��)�ķ���(w��)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Q�ɟo�����ڵ�“���(hu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ǣ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�“���(hu��)”��ǰ��Ȼ�ն��o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(w��)�Č�(du��)��ֻ���^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Ų�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ò��ɞ�“�A��(j��)”��“���w”����“�h��”�Ĺ���[6]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˱��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(d��o)�µĽY(ji��)���ǣ��vȻ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Ŀ�̖(h��o)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ڿ��^�τ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ij��(y��n)ɫ�������{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Č���֮�S����˲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ж��r(ji��)ֵ��Ԋ�W(xu��)���}��
2.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
����f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Ŀ�̖(h��o)���Ʈa(ch��n)��Σ�U(xi��n)����ô��“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�\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�ο�һ�º��ߵİl(f��)��ʷ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ʷ�ϵ�“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ArtforArt’ssake��һ�Z����19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ڵķ���С�f�Ҹ���~���c�h˹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˼�똋(g��u)����Ч�ĺ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�˲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Ӣ��Ψ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ء�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Փؕ�I(xi��n)�^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e�Ե�˥�ࡷ�@ƪ��(du��)Ԓ����Ψ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еļ��Jָ����“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֮�ⲻ���F(xi��n)�κΖ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һ���Ъ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Ҽ��ⰴ�Լ���·���l(f��)չ”�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x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“ˇ�g(sh��)Խ����Խ���뻯����Խ���҂���ʾ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��“��ߵ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f��)?d��n)����һ�N��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Ǐ��κ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飬���κθ��е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κ����X���еõ�����Ė|��”[7]��
�@һ��Փ����ʾ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ϡ����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څ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c���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ľ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ăr(ji��)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횳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ǣ�“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Ŀ�̖(h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ȱ�������˞���Д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c���¡�ˇ�g(sh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mȻ�ʬF(xi��n)��һ�N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o�����г־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Փ�Q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]֮��ȥ�Ă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܆����˵ĵ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˘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Ă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죬ˇ�g(sh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Ҳ�DZ�Ȼ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Ó�x�˾��w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ֻ���ǟoԴ֮ˮ���o��֮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ĵ��¾S�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ñ�“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�Д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ɷN����ƫ�H����Փ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(sh��)��һֱ����“��ˇ����Փ”�Q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H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еĴ��ƞE���ṩ�˱��o(h��)��Ҳˇ�g(sh��)�ҜS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R(sh��)�ΑB(t��i)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“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ҵ����ұ��o(h��)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u)�[Ó���οֲ����x�ͽ�(j��ng)��(j��)�Ѓ~���x��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һ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ò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̭��Σ�U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r�����б�Ҫ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A���D(z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c����Փ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ڵĸ�Դ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P(y��ng)һ�N�µăr(ji��)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Ԇ��}���҄e�ӵ�˼�����L�c(di��n)��
3.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^
“ˇ�g(sh��)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Ժͳ䌍(sh��)�С��nj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Ŀ϶���ף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Ի���”����ڡ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־���е��@�����Ԟ��҂�˼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r(ji��)ֵ���}ָʾ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µķ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עˇ�g(sh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@ͬ�r(sh��)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֮��(zh��ng)�ÓQ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c“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֮��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sh��)�`�Ƕȷքe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@Щ��Փ��߉ȱ�ݺ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ֵ����ҕ���Д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—“—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�
��(sh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�ٌW(xu��)�߱��_(d��)�^��Ƶ�Ҋ�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҄e����Ү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“�赸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�푘��ġ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[8]�����^��һ�Z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“����”ָ�����ʮ�ּ��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҂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P(y��ng)��“����”�s�ֲ��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ľ��衣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҂���(du��)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Д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c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Ѫ��(li��n)ϵ���ɴ˳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Եó��ĽY(ji��)Փ�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鱾λ������О�ּ?x��)w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һ�T �X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ͨ�^עҕ���w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�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o�ε����ɶ�Ŭ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֮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ǰ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Ҏ(gu��)��֧��Ľ�(j��ng)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֮��߀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ΑB(t��i)��ͬ�s�挍(sh��)���ڵij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@Ȼ�����ͨ�_(d��)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r(sh��)һ�Nֵ����ҕ��;�����@�䌍(sh��)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Ȫ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Ҳ��ֻ�� 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ȿ�Ȼ���_���˵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鱾λ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ǰ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o���ҵ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֮̎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•�_�m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{(di��o)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Ī����֮���Ԍ�(du��)�˂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H�У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п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ɞ��H�ܵ��Ѱ顣[11]�@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Ě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N�塢�Ԅe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ij�Խ���ԃ�(n��i)�ڵķ�ʽ�M(j��n)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sҲ��˶����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˵���О�ּ?x��)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κ΄e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ʽ����Ӱ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(sh��)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쪚(d��)���һ��(y��u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ڼ�(x��)�±��^�^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ʽ�h˹���˵ó����µĽY(ji��)Փ��“�����ĺ��Ҽ��ܰ��҂�Ͷ��һ�N�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һ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^�L�Ľ��f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횽�(j��ng)�^����ij�˼���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@�ӵ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Ԋ������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ע�⣬����ʹ�҂��е��dȤ��ijЩ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Ӱ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ǡ�����@�r(sh��)��ƽ��߀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ҡ�”[9]�@�Ĵ_�ǰ���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ֻ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ǰ���£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⡶�Yӛ•��ӛ���е�“Ψ�����ܞ��”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(hu��)��Ɍ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鱯���Q��֮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ڡ�ʧȥ�ˌ�(du��)�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ڵ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ˌ�(du��)�˵���е�ġ�����٬F(xi��n)�c��(chu��ng)�죬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@�ßo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гɞ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Σ�U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ָ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ӹ��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쾳�صľ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Ԓ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 ���t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`֮�o���S���Ă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c 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o��֮�g���ڶ̕��c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ͨ�Ę���———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׃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��鷽����“ˇ�g(sh��)��Ʒ��Փ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ں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x����һ�N�Ҹ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ʽ�o�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(j��ng)���ص��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J(r��n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ܵ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硣”[3]ˇ�g(sh��)ʷ�ҵ��@��Ԓǡ����ֵ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(bi��o)���H��ϣ���ɞ�ؚ���o���ߵ�ο�壬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ɞ�һ�N�e�O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Ĺ��ܲ��H�ǎ������őnጿ����Dz�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F(xi��n)�ڌ�(du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Ʋ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Ĵ_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�ʷ�o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@һ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(g��)�w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ǟo���S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(sh��)�`�Ĵ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�˵ķ�ʽ��Խ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Ρ��ڽ��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֮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߳�����Փ�c����Փ���^���λ\֮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φ�������(q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���ĵ�һ�x�����@ͬ�r(sh��)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�˂��Ű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ͬһ�ԣ��Ŝ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c�o�ľ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ؚ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Ī���•�w�����f��“ÿһ��(g��)�µġ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Ʒ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˶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”[10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ķ�ʽ��(sh��)�`���@һ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�ij�N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@Ҳ���҂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չ�_������Փ�c����Փ֮��(zh��ng)�Ļش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f�܉༤��(l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c�l(f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ě_��(d��ng)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Ļ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ؕ�I(xi��n)��Ԓ����ô��ֻ��“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ˇ�g(sh��)”�Ŝ�(zh��n)�_�ذ���ס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ăr(ji��)ֵ�cʹ�����Ş��҂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Č��Ԇ��}�ṩ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x�ĽǶȣ�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ϼ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ҕ�c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�����īI(xi��n)
[1][�W]�۵��A•�h˹����.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———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c�h.��I(y��)�Σ��g.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1980.
[2]����.�o����Փ.��������.�Ї����W(xu��)ʷ�Y���x��.�Ϻ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8.
[3][��]�ſƷ��з�.ˇ�g(sh��)�c�����ڽ�.�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.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磬1989.
[4][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•˹��.���c��.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.�Ϻ����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1991.
[5][��]Ү����•÷�~��.�������.��ɼ���g.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3.
[6]�����.�F(xi��n)��ҕҰ�е�Ψ�����x.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о�.2004��4��.
[7][Ӣ]������.�e�Ե�˥��.ʒ�����g.�w��ƽ����.����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.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00.
[8][��]�e����Ү��.�˵�ū���c����.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.�Fꖣ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磬1994.
[9][��]�_��•�_�m.�_��•�_�m����ɢ�ļ�.��ɼ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g.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湫˾��1999.
[10][��]Ī���•�w��.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ζ.�������g.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ij����磬1998.
���ľ�̖(h��o)��10137
�Y�����d
Փ�İl(f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朽ӣ�http://lk138.cn/jiaoyulunwen/xuekejiaoyulunwen/10137.html
Փ�İl(f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̲Č���
��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
- 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W(xu��)���ƌW(xu��)̽�����ܵİl(f��)չ��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W(xu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n�ÌW(xu��)��(x��)�u(p��ng)�r(ji��)�ĸ��о�
- ����ɳ�၆:�����ɹ��D(zhu��n)�͵Ė|�WС��
- ��PBL�̌W(xu��)(li��n)�Ϸ��D(zhu��n)�n�����t(y��)�W(xu��)�̌W(xu��)�еđ�(y��ng)��
- ����УӢ�Z��Ϣ���̌W(xu��)�l(f��)չ�F(xi��n)���c���}�о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