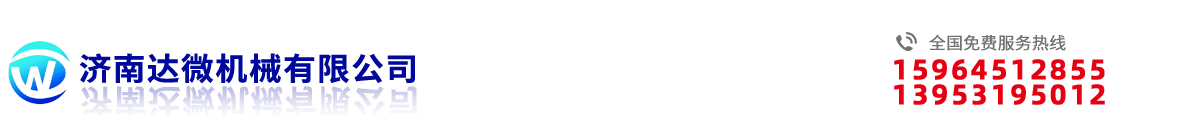ОчД·Аӯ•юЧhј°ЦРУўҪ»Йж
°l(fЁЎ)Іј•rйgЈә2015-04-06 08:32
ХӘТӘЈә20КАјoіхЈ¬ЛщЦ^Х{(diЁӨo)ҪвОчІШөШ·ҪЕc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кP(guЁЎn)ПөөДОчД·Аӯ•юЧhКЗУўҮшНЖРР°Фҷа(quЁўn)ЦчБxЈ¬ЖуҲD·ЦБСОчІШГ“лxЦРҮшөДЧҫБУРРһйЎЈОчД·Аӯ•юЧhұM№ЬЧоҪKТФК§”Ў¶шёжҪKЈ¬ө«ҢҰ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ЕcОчІШөШ·ҪөДкP(guЁЎn)Пө®a(chЁЈn)ЙъБЛҗәБУУ°н‘әНҮАЦШәу№ыЎЈҪьТ»ӮҖКАјoТФҒнЈ¬ҫіНв”іҢҰ„ЭБҰј°Я_ЩҮ·ЦБСјҜҲFТФ·З·ЁөД“ОчД·АӯІЭјs”әН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һйТА“ю(jЁҙ)Ј¬ҲDЦ\ОчІШ“ӘҡБў”ЎЈ·З·ЁөД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ТІіЙһйЖщҪсһйЦ№ИФОҙҪвӣQөДЦРУЎЯ…ҪзҶ–о}®a(chЁЈn)ЙъөДёщФҙЈ¬Жд„қ¶Ё…^(qЁұ)УтТІіЙһйЦРҮшғHҙжөДк‘В·Оҙ¶ЁҪзЦР ҺЧhЧоҙуөДТ»үKөШ·ҪЈ¬іЙһйУ°н‘ЦРУЎғЙҮшкP(guЁЎn)ПөХэіЈ°l(fЁЎ)Х№өДидифЎЈұMФзҪвӣQЯ…ҪзҶ–о}Ј¬ТСҪӣ(jЁ©ng)іЙһйЦРУЎғЙҮшөД№ІН¬ФёНыЈ¬ЦРУЎлp·Ҫ‘Ә(yЁ©ng)ід·ЦЧрЦШҡvК·КВҢҚЈ¬ТФ·ЁВЙһйТА“ю(jЁҙ)Ј¬ТФғЙҮшкP(guЁЎn)ПөҙуҫЦәНғЙҮшИЛГсёщұҫәНйLЯhАыТжһйёщұҫіц°l(fЁЎ)ьcұMФзҪвӣQЦРУЎЯ…ҪзҶ–о}ЎЈ
кP(guЁЎn)жIФ~ЈәОчД·Аӯ•юЧh,ЦРУўҪ»Йж,ҮшлHкP(guЁЎn)ПөҙTКҝХ“ОД
кP(guЁЎn)жIФ~ЈәОчД·Аӯ•юЧh,ЦРУўҪ»Йж,ҮшлHкP(guЁЎn)ПөҙTКҝХ“ОД
¶аДкҒнЈ¬ЦРҮшј°ГАЎўУЎЎўУўЎў·ЁөИҮшөДҢЈјТҢW(xuЁҰ)ХЯҢҰОчД·Аӯ•юЧhј°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өИҶ–о}ЯMРРБЛұИЭ^ЙоИлөДСРҫҝЎЈўЩө«ҢҰЯ@Т»ЦШҙуҡvК·КВјюИФУРЯMТ»ІҪМҪУ‘өДұШТӘЎЈұҫОДҢўОчД·Аӯ•юЧhәН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ЦГУЪҮшлHөШҫүХюЦОұіҫ°ПВҝјІмЈ¬ЙоҝМЖКОц“ОчД·АӯІЭјs”әН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өД·З·ЁРФЈ¬ід·ЦҪТВ¶УўҮшј°ОчІШ·ЦБС„ЭБҰөДкҺЦ\Ј¬һйЦРУЎғЙҮшұMФзҪвӣQЦРУЎЯ…ҪзҶ–о}МṩҡvК·ҪииbәН·ЁАнТА“ю(jЁҙ)ЎЈ
Т»ЎўУўҮшФЪ•юЗ°өДІЩҝvЕcҝШЦЖ
ЦРИAГсҮшіЙБўәуЈ¬іцУЪөШҫүХюЦОөДРиТӘЈ¬УўҮш“ҹбРД”ҙЯҙЩЈ¬ІўТФІ»іРХJЦРИAГсҮшҒнГ{ЖИЦРҮшН¬ТвХЩй_Х{(diЁӨo)ҪвГсҮшЦРСлЕcОчІШөШ·ҪкP(guЁЎn)ПөөД•юЧhЈ¬ЖдЦчТӘТвҲDКЗНЖЯMТФ“8·17ӮдНьдӣ”һйЦчТӘғИ(nЁЁi)ИЭөДУўҮшРВөДЗЦІШ‘р(zhЁӨn)ВФЎЈУўҮшФҮҲD°СЦРҮшОчІШј{ИлУўҢЩУЎ¶ИөД·А„Х(wЁҙ)уwПөЈ¬І»ФКФS°ьАЁЦРҮшФЪғИ(nЁЁi)өДИОәОҮшјТТФИОәОГыБxЎўИОәОНҫҸҪИҫЦёОчІШЈ¬К№ОчІШіЙһйГыБxЙПКЗЦРҮшЧЪЦчҷа(quЁўn)Ц®ПВөДЧФЦОҮшЈ¬¶шҢҚЩ|(zhЁ¬)ЙПМҺУЪҪ^ҢҰТАҝҝУўУЎХюё®өДөШО»Ј¬ТФЕЕіэИОәОҒнЧФұұ·ҪҢҰУўҢЩУЎ¶ИөД“НюГ{”ЎЈ
һйБЛІЩҝШ•юЧhЈ¬УўҮшФЪ•юЗ°ҫН•юЧhөД·ҪКҪЎўҙъұнИЛЯxЎўөШьcөИҸҠУІёЙоA(yЁҙ)Ј¬Я@ЖдЦРөД“НвҪ»КЦ¶ОЎўҸҠҷа(quЁўn)ХюЦОәНйgХҷ»о„У¶јКЗОе»Ё°ЛйTЎўеeҫCҸН(fЁҙ)лsөДұнСЭ”ЎЈўЩЦм –өдФшФЪҪoёсАЧөДлҠҲуЦРМбіцЈ¬УўҮшЎўЦРҮшЎўОчІШөДИэ·Ҫ…f(xiЁҰ)ЧhҢўКЗЧоәГөДҪвӣQЮk·ЁЈ¬¶шФЪУЎ¶ИЯMРРХ„ЕРҢўКЗЯ_іЙЯ@Т»…f(xiЁҰ)ЧhөДУРТжй_¶ЛЈ¬јҙК№К§”ЎТІҢўК№УўҮшФЪЕЕіэЦРҮшөДЗйӣrПВЕcОчІШЯMРРөДХ„ЕРЦРМҺУЪғһ(yЁӯu)ФҪөДөШО»ЎЈУўҮшҸҠЖИ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ҪУКЬОчІШөШ·ҪЧчһй•юЧhХэКҪөЪИэ·Ҫ…ў•юЈ¬ЙГЧФёьёД•юЧhөШьcУЪУЎ¶ИОчД·АӯЈ¬¶шЗТТӘЗу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ұШнҡЯxЕЙУЙУўҮшХJҝЙөДУHУўИЛКҝЧчһйХ„ЕРҙъұнөИЎЈБнНвЈ¬УўҮшҙъұнЯҖЕc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Па»Ҙ№ҙҪY(jiЁҰ)Ј¬№ІН¬ІЯ„қҢҰё¶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өД·Ҫ°ёЈ¬№ВБў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Іўё`ИЎПакP(guЁЎn)ЩYБПЎЈХэИзғИ(nЁЁi)ҫS –·сRҝЛЛ№нf –ЛщХfЈә“ҮшјТөДЬӣИхК№ЦРҮшІ»өГІ»өҪ•юЧhЧАЙПҒнЎЈЦРҮшөДЬӣИхјУЙПУўҮшөД———ТІ°ьАЁыңҝЛсRәйұҫИЛөД———НвҪ»·ҪГжөДёЯүәКЦ¶ОУЦ°СЦРҮшНПФЪДЗАпЎЈ”ўЪ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ұ»ЖИ…ўјУУЙУўҮшҝШЦЖЎўТвҲD·ЦБСЦРҮшОчІШөДХ„ЕРЎЈ
1.ТӘЗуОчІШөШ·ҪХюё®ұШнҡЧчһй•юЧhХэКҪөЪИэ·Ҫ…ў•юЎЈ
УўҮшһйЦЖФмЛщЦ^өД“ОчІШӘҡБў”ЭӣХ“Ј¬ҲФіЦТӘҪoУиОчІШөШ·ҪХюё®ЧчһйХэКҪҙъұн…ўјУ•юЧhөДөШО»Ј¬ТФАыУЪОчІШөШ·ҪЕcУўҮшј°ГсҮшЦРСлҙъұнТ»ЖрФЪ—lјsЙПәһЧЦЈ¬ЖдДҝөДФЪУЪМбЙэОчІШөДөШО»Ј¬К№Ц®ЕcЦРҮшЎўУўҮшЖҪөИ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·ЗіЈЗеіюУўҮшөДлUҗәУГРДЈ¬ҲФіЦОчІШКЗЦРҮшөДТ»Іҝ·ЦЈ¬Мбіц“ПИУЙЦРУў•юЙМУҶЧhәуЈ¬ФЩНЁЦӘОчІШөШ·Ҫ”»т“ФКФSОчІШөШ·ҪёҪҺ§өШФЪ—lјsЙПәһЧЦ”өИҪЁЧhЎЈўЫИ»¶шЈ¬УўҮшҸҠУІҫЬҪ^БЛ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өДЯ@Т»Хэ®”ТӘЗуәНҮАХэБўҲцЈ¬ТӘЗуОчІШөШ·ҪХюё®ұШнҡЧчһй•юЧhөДТ»·ҪТФЖҪөИөДөШО»…ўјУЈ¬ІўНюГ{ХfҙЛ·NЮk·ЁЈ¬УўҮш„ЭФЪұШРРЈ¬ИзЦРҮшІ»ДЬН¬ТвЈ¬•юЧhЦ®КВЦ»әГЧчБT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»ГПлНЁЯ^УўҮшХ{(diЁӨo)ҪвТФҪвӣQОчІШҶ–о}Ј¬ГжҢҰУўҮшөДҸҠҷа(quЁўn)ј°ҹoАнТӘ’¶Ј¬І»ёТЕcЖдЦұҪУҢҰҝ№Ј¬ұ»ЖИЧҢІҪЎЈө«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ҢҰҙЛәуУўҮшЛщВ•·QЦРҮшХюё®іРХJИэ·ҪЖҪөИҙрҸН(fЁҙ)УўҮшЈә“ЩFҮшХюё®ХJһйұҫҮшТСіРХJИэ·ҪЖҪөИЛЖУРХ`•юЈ¬»тПөЧgОДЕӘеeЈ¬ХҲІйХХёьХэһйЕО”ЎЈўЬұM№ЬУўҮшТ»ФЩҸҠУІЈ¬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ИФИ»ғHН¬ТвОчІШөШ·ҪХюё®ҙъұн“ёҪН¬ЕcЧh”Ј¬ІўЦ»ДЬ“ёҪәһ”УРкP(guЁЎn)ОДјюЎЈўЩјҙК№ФЪУўҮшНюГ{ИфІ»Н¬ТвУўҮш°ІЕЕҫНЦұҪУЕc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ЙМХ„•rЈ¬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ИФУ–(xЁҙn)БоЦРСлҙъұнкҗЩO·¶ФЪ•юЧhәһЧhҶ–о}ЙП‘Ә(yЁ©ng)БҰ ҺЦРЎўУўІўБРЈ¬ІШҶTлSН¬әһСәЎЈ
2.ЙГЧФёьёД•юЧhөШьcУЪОчД·АӯЎЈ
һйБЛұгУЪІЩҝv•юЧhЯMіМЈ¬УўҮшҫЬҪ^БЛГсҮшЦРСлХюё®“•юЧhөШьc¶ЁФЪұұҫ©»тӮҗ¶Ш”өДМбЧhЎЈУўҮшПИКЗХf•юЧhөШьcФO(shЁЁ)ФЪУЎ¶ИҙујӘҺXЈ¬әуһйБЛұO(jiЁЎn)ҝШ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НЁУҚІў·вжiҢҰНвПыПўЈ¬ЙГЧФҢў•юЧhөШьcёДФЪЯhлxУЎІШҪ»НЁТӘөАЗТИAИЛәНІШЧеН¬°ыҫУЧЎЭ^ЙЩөДОчД·АӯЈ¬ТтһйУўҮш“ФЪДЗАпҝЙТФК©јУёьҙуөДУ°н‘ҝШЦЖ•юЧhЯMіМЈ¬Н¬•rОчІШҙъұнТІІ»•юИзФЪҙујӘҺXДЗҳУКЬөҪЦРҮшИЛкҺЦ\өДУ°н‘”Ј¬ўЪІўҸҠЖИ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ҹo—lјюҪУКЬБЛёДФO(shЁЁ)өД•юЧhөДөШьcЎЈ
3.МфЯxГсҮшЦРСлХюё®•юЧhҙъұнЎЈ
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ЧоіхИОГьЗ°ЗесvІШҙуіјңШЧЪҲтһй•юЧhҙъұнЈ¬ө«ңШЧЪҲтФЪөГЦӘФ¬КА„PТСН¬ТвУў·ҪөДМбЧhЈ¬•юЧhөШьcФO(shЁЁ)ФЪУЎ¶ИҙујӘҺX•rЈ¬ҲФӣQЮoВҡЈ¬ҫЬҪ^іцПҜҙЛҙО•юЧh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УЦЯxЕЙКмПӨОчІШКВ„Х(wЁҙ)ІўФЪЕcУўҮшХ„ЕРЦРҪӣ(jЁ©ng)тһШSё»өДҸҲКaМДЈ¬І»БП…sТтЖд“КмПӨІШКВЎўҫ«ГчҸҠУІ”өИФӯТтұ»УўҮшҫЬҪ^ЎЈУўҮшЦёГыТӘЗу“ТФЧФЦЖәННЁЗйЯ_Ан¶шЙоКЬУўИЛПІҡgөДкҗЩO·¶”(ФшФЪУўҮшИОоI(lЁ«ng)КВ)ЧчһйГсҮшЦРСлХюё®“ОчІШЧhјsИ«ҷа(quЁўn)ҢЈҶT”Ј¬ўЫ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УЦНЧ…f(xiЁҰ)НЛЧҢёДЕЙкҗЩO·¶һй•юЧhИ«ҷа(quЁўn)ҙъұнЈ¬Н¬•rИОГьәъқhГсһйХ„ЕРҙъұнЈ¬ЕcкҗПнУР№ІН¬ҷа(quЁўn)БҰЈ¬ө«УЦФвөҪУўҮшҫЬҪ^Ј¬ҹoДОУЦёДЕЙНхәЈЖҪһйХ„ЕРёұҙъұнЎЈ
4.Еc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Па№ҙҪY(jiЁҰ)№ІН¬ІЯ„қҢҰё¶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өД·Ҫ°ёЎЈ
ФзФЪ•юЧhЗ°3ӮҖФВЈ¬УўҮшҫНҙЯҙЩОчІШөШ·ҪУHУўЕЙИЛОпПДФъЪsё°ҒҶ–|Ј¬Н¬•rЕЙіцКмПӨОчІШөДШҗ –ЕcЖд•юГж№ІН¬ңКӮдПакP(guЁЎn)ІДБПЈ¬·eҳOІЯ„қҢўОчІШҸДЦРҮш·ЦБСіцИҘөДкҺЦ\ЎЈШҗ –іРХJЈә“®”ЦРҮшИ«ҷа(quЁўn)ҙъұн¶әБфЦРҮш•rЈ¬ОТәНПДФъФЪҪӯЧО•юәПЈ¬Іў„сЖдЛСјҜУРкP(guЁЎn)ТФЗ°ЦРҮшЕcОчІШҪ»ЙжТФј°к‘Аm(xЁҙ)ұ»ЦРҮшХјоI(lЁ«ng)¶ш¬F(xiЁӨn)ҪсОчІШТӘЗуҡwЯҖөДёч·NЩYБПЈ¬”yҺ§ё°•юЎЈ”ўЬ°ҙХХШҗ –өДТӘЗуЈ¬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ЛСјҜБЛФS¶аЩYБПІўПИУЪ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өҪ•юЎЈ®”ОчІШөШ·ҪҙъұнөЦЯ_ОчД·Аӯ•rЈ¬ыңҝЛсRәйәНШҗ –өИИЛҢҰПДФъТ»РРҹбЗйҪУҙэЈ¬лp·Ҫ¶аҙОҪ»Х„Ј¬ҢҰ•юЧhғИ(nЁЁi)ИЭЎўДҝөДј°ІЯВФҫщЧчБЛЦЬГЬөДСРҫҝЕcІҝКрЈ¬Іўҫ«РДІЯ„қБЛ•юЧhөДХЩй_Юk·Ёј°ҢҰё¶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өД·Ҫ°ёЎЈўЭУўҮш•юЗ°ұг°С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АОАОҝШЦЖФЪЧФјәКЦЦРЎЈ
5.№ВБў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Ј¬ё`ИЎПакP(guЁЎn)ЩYБПЎЈ
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өҪЯ_әуЈ¬УўҮшО©ҝЦ°l(fЁЎ)ЙъІ»АыУЪЧФјәөДЧғ№КЈ¬ҫ№ТФЕгН¬ЎўХРҙэОчІШөШ·ҪҙъұнһйУЙЈ¬ИХТ№ұO(jiЁЎn)Т•ПДФъТ»РРЈ¬І»ФКФS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Еc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ҪУУ|Ј¬ЙхЦБҪыЦ№лp·ҪНЁРЕЎЈкҗЩO·¶ФшлҠёж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УўҮшИЛҢҰПДФъөИИЛ°ө·АЙхГЬЈ¬І»ЧҢЛыӮғЕcкҗҶОӘҡ•юГжЎЈУўҮшЯҖПтЦРҮшәЈкP(guЁЎn)ҝӮКрУўј®¶җ„Х(wЁҙ)ЛҫК©јУүәБҰЈ¬ХЩ»ШкҗЩO·¶ЛщЖёУГөДІјф”КҝЈ¬ЖуҲD·ЦБСкҗЩO·¶өДЦЗДТҲFЎЈкҗЩO·¶Еc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НщҒнөДТ»ЗРлҠОДҫщУЙУўҢЩУЎ¶ИлҠҲуҫЦКХ°l(fЁЎ)Ј¬ЛыӮғНөё`БЛкҗЩO·¶Еc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өДНщҒнәҜјюЈ¬ҢҰЦР·ҪөД·Ҫ°ёЎўІЯВФБЛИзЦёХЖЎЈкҗЩO·¶ФшХfЈә“ОТөДТ»ЗР№ӨЧч¶јУЙЧФјә„УКЦЈ¬өГІ»өҪИОәОНвҒнҺНЦъЈ¬№ВЬҠЧч‘р(zhЁӨn)Ј¬ҢҰё¶әГҺЧӮҖ”іКЦЎЈ”ўЮ
¶юЎў•юЧh ҺЧhҪ№ьcј°УўҢҰІШ“ӘҡБў”өД‘B(tЁӨi)¶И
1913Дк10ФВ13ИХЈ¬ЦРЎўУўј°ОчІШөШ·ҪҙъұнФЪОчД·АӯХЩй_өЪТ»ҙО•юЧhЎЈіцПҜ•юЧhөДЦчТӘИЛҶTУРЈә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кҗЩO·¶Ј»УўҮшҙъұнУўУЎХюё®Нв„Х(wЁҙ)ҙуіјыңҝЛсRәйЈ¬оҷҶ–УўсvеaҪрРРХю№ЩҶTШҗ –Ј»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ПДФъөИЎЈ•юЧhНкИ«ТАХХУўҮшоA(yЁҙ)ПИІЯ„қөДКВн—ЯMРРЈәПИУЙПДФъМбіц“ОчІШӘҡБў”·Ҫ°ёЈ¬ТэЖрГсҮшЦРСлҙъұнөДҸҠБТ·ҙҢҰЈ¬ыңҝЛсRәйіГҷCҫУЦРОУРэЈ¬К№Х„ЕРЯMИлУўҮшоA(yЁҙ)ФO(shЁЁ)өДЬүөАЈ¬ўЩХTҢ§(dЁЈo)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ВдИлЖдоA(yЁҙ)ФO(shЁЁ)өДПЭЪеЎЈ
1.ОчІШөШ·Ҫҙъұн’Ғіц“ОчІШӘҡБў”ЦҮХ“ЎЈПДФъ°ҙХХЕcУў·ҪКВПИГШГЬЙМНЧөД·Ҫ°ёЈ¬МбіцкP(guЁЎn)УЪОчІШөШО»Ҷ–о}ЎўҪ®ҪзҶ–о}ЎўІШУЎЩQ(mЁӨo)ТЧҶ–о}ЎўЦРҮшсvІШҶ–о}ЎўЧЪҪМҶ–о}ј°Щrғ”?shЁҙ)ИТӘЗуЧчһй•юЧhУ‘Х“өДТА“ю(jЁҙ)ЎЈЯ@6ьcТӘЗуНкИ«·сХJОчІШһйЦРҮшөШ·Ҫ…^(qЁұ)УтөДҡvК·КВҢҚЈ¬НэҲDҸUіэЦРУўғЙҮшЦ®З°әһКрөДіРХJОчІШКЗЦРҮшТ»Іҝ·ЦөДёч·N—lјsЈ¬НкИ«ёо”аОчІШөШ·ҪЕcЦРҮшЦРСлХюё®өДТ»ЗРкP(guЁЎn)ПөЎЈЖдДҝөДҫНКЗ°СОчІШј°ЖдЛыЛДКЎІШ…^(qЁұ)ҸДЦРҮш·ЦБСіцИҘЈ¬ҪЁБўТ»ӮҖНкИ«ТАёҪУўҮшөДЛщЦ^ӘҡБў
өД“ОчІШ”Ј¬ІўФҮҲDАыУГИэ·ҪіРХJөДЎўҫЯУР·ЁВЙР§БҰөДҮшлH—lјsөДРОКҪәП·Ё»ҜЎЈПДФъЛщМбіцөДІШ…^(qЁұ)Н»ЖЖБЛЗеХюё®Лщ„қ¶ЁУЙОчІШөШ·Ҫ№ЬЭ ЦОАнөД·¶ҮъЈ¬ЖуҲDТ»ЕeНМІў¬F(xiЁӨn)ҪсёКЎўЗаЎўҙЁЎўөб4КЎөДІШ…^(qЁұ)ЎЈ
2.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өДсgҸН(fЁҙ)ТвТҠЎЈкҗЩO·¶”аИ»·сӣQБЛПДФъөДҹoАнТӘЗуЈ¬ІўФЪ•юәуҫoјұЦВлҠ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Јә“ОчІШҙъұнБРЧhТФҒнЈ¬‘B(tЁӨi)¶И®җіЈҸҠУІЈ¬ҢҰУЪОТҮш·ҪГжМбіц—lјюЈ¬ЖдҪиҝЪУЪЗ°ЗеДіҙуҶTЯMұшОчІШЈ¬ЬҠјoІ»ҮАЈ¬ҡ§ҸRгЮұшЈ¬ёРЗйЙхҗәЈ¬І»ФёіРЦZЈ¬ІўІ»ХJЦРҮшФЪОчІШУРЦчҷа(quЁўn)Ц®РРК№ЎЈ”ўЪҲуёжБЛОчІШөШ·ҪөД‘B(tЁӨi)¶Иј°УўҮшІЩҝv•юЧhөИКВн—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лSјҙПткҗЩO·¶өИЧчіц·сӣQОчІШ6—lөДГчҙ_ЦёКҫЎЈкҗЩO·¶ёщ“ю(jЁҙ)ЦёКҫЈ¬ҸДОчІШКЗЦРҮшІ»ҝЙ·ЦёоөДоI(lЁ«ng)НБЯ@Т»ҡvК·КВҢҚіц°l(fЁЎ)Ј¬Ф”ұMкUГчБЛОчІШЕcЦРСлХюё®өДл`ҢЩкP(guЁЎn)ПөЈ¬ІўЦШЙк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ҢўТ»ИзҡvҙъЦРҮшЦРСлХюё®ҢҰОчІШөШ·ҪҢҚРРЦчҷа(quЁўn)№ЬЭ Ј¬“ю(jЁҙ)АнсgівБЛПДФъөДЦҮХ“ЎЈўЫ
3.·ЦЖзЕc ҺЧhҪ№ьc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ЕcОчІШөШ·ҪөД·ЦЖзәН ҺЧhҪ№ьcЦчТӘјҜЦРФЪғЙӮҖҶ–о}ЙПЎЈТ»КЗОчІШөДЦчҷа(quЁўn)Ј¬Йжј°ОчІШөДХюЦОөШО»ЎўЦРСлХюё®№ЬЭ ҷа(quЁўn)ПЮЎўЦРСлсvІШ№ЩҶTј°ЦРСлсvЬҠөИЎЈОчІШөШ·ҪҙъұнҸДёщұҫЙП·сХJБЛОчІШЕcЦРҮшөДкP(guЁЎn)ПөЈ¬ТӘЗуӘҡБўЈ»·сХJіэУЎІШ—lјsЦ®НвөДЦРУўЛщәһУҶөДкP(guЁЎn)УЪОчІШөДИОәО—lјsЈ»Ц»ДЬФЪОчІШФКФSөДЗйӣrПВЈ¬іЦУРОчІШЧoХХөДЦРҮшИЛІЕДЬЯMИлОчІШ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ҲФіЦөД»щұҫФӯ„tКЗ»ЦҸН(fЁҙ)ФЪІШјИУРЦОҷа(quЁўn)Ј»ҸҠХ{(diЁӨo)СУАm(xЁҙ)ЗеҙъсvІШҙуіјЦЖ¶ИЈ¬УЙГсҮшЦРСлОҜЕЙсvІШ№ЩҶTЕcсvЬҠЈ»ҸҠХ{(diЁӨo)ОчІШһйЦРҮшТ»Іҝ·ЦЈ¬ҝЙІ»ёДРРКЎЈ¬ө«ИФ°ҙМШ„eРРХю…^(qЁұ)№ЬЭ ЕcЦОАнЎЈ¶юКЗОчІШөШ…^(qЁұ)өД·¶ҮъЎЈОчІШөШ·ҪҙъұнҢўОчІШј°ТФНщТ»ЦұҢЩУЪЛДҙЁ№ЬЭ өД°НМБЎўАнМБЎўҙтјэ tј°ЗаәЈЎўёКГCЎўФЖДПөИөШІШ…^(qЁұ)Ј¬И«Іҝј{ИлОчІШөД·¶ҮъЈ¬ҙуҙуі¬Я^БЛЗ°ЗесvІШҙуіјөД№ЬЭ …^(qЁұ)Ут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„tХJһйОчІШ…^(qЁұ)Ут?qЁұ)ўҒнөД„қ·ЦЮk·ЁнҡХХЗ°ЗеёөбФ¶kЛщАLЦ®ІШКЎҲD(јҙЗеіҜРыҪy(tЁҜng)¶юДкәЛңКөДОчҝөКЎЕcОчІШРРХю…^(qЁұ)„қҪзҫҖҲD)әЛЙМЈ¬ТФҪӯЯ_һйҪзЎЈҸД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ПДФъөДБщьcТӘЗуәН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өДсgҸН(fЁҙ)ТвТҠҒнҝҙЈ¬лp·ҪөДХ„ЕР—lјю‘ТКвМ«ҙ󣬕юЧhПЭИлҪ©ҫЦЎЈ
4.УўҮшҢҰОчІШөШ·Ҫ“ӘҡБў”өД‘B(tЁӨi)¶ИЎЈГсҮшіхЖЪЈ¬ОчІШөШ·Ҫ·ЦБС„ЭБҰТ»ЦұФҮҲDНЁЯ^ТАҝҝУўҮшЦ§іЦҢҚ¬F(xiЁӨn)“ӘҡБў”ЎЈҸДПДФъФЪөЪТ»ҙО•юЧhЙПЛщМбіцөДУГУўОДЧ«Ң‘өД“ОчІШТвТҠ•ш”ЎўЛщУГУўҮш»КјТөШАнҢW(xuЁҰ)•юАLЦЖөД“ОчІШЕcаҸҫіҲD”һй„қҪзҲDЎўЛщМбіцөДОчІШ…^(qЁұ)УтЕc…f(xiЁҰ)ЦъыңҝЛсRәйЧhјsөДУў·ҪоҷҶ–Шҗ –ЦчҸҲөДОчІШ…^(qЁұ)Ут»щұҫПаН¬өИИэьcҒнҝҙЈ¬УўҮшөДҙ_Ц§іЦБЛОчІШөД“ӘҡБў”»о„УЎЈҙЛҙОІШ·ҪЛщМб—lҝоУўОДұҫЈ¬ОДЧЦЙхјСЈ¬п@һйУўИЛЦчЦ\ЎЈө«КЗЈ¬№PХЯХJһйЈ¬УўҮшЦ»КЗід·ЦАыУГОчІШөШ·Ҫ·ЦБС„ЭБҰөД“ӘҡБў”РДАнЈ¬ҢўЧФјәөДкҺЦ\л[ІШФЪһйОчІШЦ\ИЎ“ӘҡБў”өД»ПЧУЦ®ПВЈ¬јЩТвҙр‘Ә(yЁ©ng)Ц§іЦОчІШ“ӘҡБў”Ј¬ТФАыУЪҢҰОчІШөШ·Ҫҙъұнј°ХыӮҖ•юЧh·ҪПтөДҝШЦЖәНјИ¶Ё·Ҫ°ёөДМбіцЎЈФӯТтУРИэЈәТ»КЗҪиҙЛАӯ”nОчІШөШ·Ҫ№ІН¬ҢҰё¶ЦРҮшЦРСлХюё®Ј¬ҪиТФұЖЖИЦРҮшЦРСлХюё®ФЪЦчҷа(quЁўn)өИЦШҙуҶ–о}ЙПЧціцЧҢІҪЈ»¶юКЗАӯ”nОчІШөШ·ҪЦЖФм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ЕcОчІШөШ·Ҫ‘ТКвөДХ„ЕР—lјюЈ¬ЦВК№•юЧhПЭИлҪ©ҫЦЈ¬“ЧҢОчІШИЛЕcЦРҮшИЛФЪТӘЗуЕc·ҙТӘЗуЦРЯMРР ҺХ“Ј¬И»әуПаҷCМбіцУў·ҪөДҪЁЧhЧчһйғЙ·NТвТҠөДәПАнНЧ…f(xiЁҰ)”Ј¬ўЩТФАыУЪУў·ҪёьәГөШТФХ{(diЁӨo)ҪвХЯөДЙн·ЭҝШЦЖ•юЧhЧЯПтЈ»ИэКЗһйУўҮшМбіц“ғИ(nЁЁi)НвІШ·Ҫ°ё”әН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ВсПВ·ь№PЎЈКВҢҚЙПЈ¬УўҮшІўІ»ПЈНыОчІШХжХэөД“ӘҡБў”ЎЈФЪОчД·Аӯ•юЧhЙПОчІШИфКЗХжХэҢҚ¬F(xiЁӨn)“ӘҡБў”Ј¬ЦРҮшоI(lЁ«ng)НБЎўЦчҷа(quЁўn)өДҪy(tЁҜng)Т»әННкХыұШИ»ФвөҪҮАЦШЖЖүДЈ¬Я@ұШҢўФвөҪ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ј°°ьАЁІШЧеН¬°ыФЪғИ(nЁЁi)өДЦРҮшёчЧеИЛГсөДҸҠБТ·ҙҢҰЈ¬ұШҢўПЖЖрТ»ҲцВ•„ЭәЖҙуөД·ҙУў¶· ҺЈ¬УўҮшйLЖЪҝаРДҪӣ(jЁ©ng) IөДФЪИAАыТжұШҢўКЬөҪҮАЦШҙт“фЈ¬Я@КЗУўҮшЛщІ»ФёТвҝҙөҪөДЎЈУўҮшИфВКПИҙтЖЖОч·ҪёчҮш“ұЈИ«ЦчБx”ТҺ(guЁ©)„tЈ¬УўҮшөДёӮ ҺҢҰКЦҢў•ю·д“н¶шИлёӮПаҝШЦЖОчІШЈ¬ОчІШТІҫНУРҝЙДЬГ“лxБЛУўҮш“ӘҡЧФҝШЦЖ”өДЬүөАЈ¬ІўҢўЯMТ»ІҪНюГ{өҪУўҮшФЪДПҒҶҙОҙук‘өДЦіГсҪy(tЁҜng)ЦОЈ¬ҢҰУўҮшФЪЦРҮшј°ҒҶЦЮДЛЦБИ«Зт‘р(zhЁӨn)ВФҢў®a(chЁЈn)ЙъҮАЦШәу№ыЈ¬ЙхЦБКЗҡ§ңзРФөДҙт“фЎЈЛщТФЈ¬ҸД®”•rөДЦРҮшј°ҮшлHӯh(huЁўn)ҫіҝҙЈ¬ОчІШХжХэ“ӘҡБў”І»·ыәПУўҮшЗЦІШРВВФјИ¶Ё·ҪбҳЈ¬п@И»УўҮшІ»•юЦ§іЦОчІШХжХэ“ӘҡБў”ЎЈ
ИэЎўОчІШ„қҪзҶ–о}ј°УўҮш’ҒіцөД“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”Еc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
1.УўҮшҮъА@ОчІШ“Ҫз„Х(wЁҙ)Ҷ–о}”ҙуЧцОДХВЎЈУў·ҪТФ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ЕcОчІШөШ·ҪҢҰУЪ“ОчІШ·¶Үъ”Іо®җҳOҙуһйҪиҝЪЈ¬Ңў•юЧhТэөҪОчІШҪз„Х(wЁҙ)Ҷ–о}ЙПЎЈФЪ11ФВ18ИХХЩй_өДөЪ¶юҙОХэКҪ•юЧhЙПЈ¬ыңҝЛсRәйМбіц“ОчІШҪзПЮЦ®„қ·Ц”КЗ•юЧh“өЪТ»ӮҖТІјҙЧоЦШТӘЦ®Ҷ–о}”Ј¬ұШПИУ‘Х“Ҫз„Х(wЁҙ)Ҷ–о}Ј¬·с„tЛыІ»ДЬҪMҝ—•юЧh“У‘Х“ЖдЛы—lҝо»тРОіЙҢҰЯ@Р©—lҝоөДУ^ьc”ЎЈПДФъБўјҙЩқН¬Уў·ҪТвТҠЈ¬ТӘЗу•юЧhЧh¶ЁЛщЦ^ЦРІШлp·Ҫ“„қҪз”Ҷ–о}Ј¬ЛыХfЈә“УЙУЪЯ…Ҫз·ЦЖзИзҙЛЦ®ҙ󣬬F(xiЁӨn)ФЪУ‘Х“ЖдЛыҶ–о}ТІӣ]УРТвБx”ЎЈўЪкҗЩO·¶„tҲФіЦЈ¬Ҫ®ҪзҶ–о}І»КЗ•юЧhөДЧhо}Ј¬‘Ә(yЁ©ng)КЧПИУ‘Х“ОчІШөДХюЦОөШО»Ҷ–о}ЎЈЛыҸҠХ{(diЁӨo)КЧПИҪвӣQОчІШЦ®“ХюЦОөШО»”Ҷ–о}ІЕ“УРЦъУЪҪвӣQЯ…ҪзҶ–о}”әН“УРАыУЪЖдЛыҶ–о}Ц®ҪвӣQ”ЎЈыңҝЛсRәйҫЬІ»Н¬ТвкҗЩO·¶өДМбЧhЈ¬ХfКІГҙ“ЛыІ»ЦӘөАФЪОчІШЦ®Я…Ҫзҙ_¶ЁЦ®З°Ј¬ОчІШЦ®ХюЦОөШО»ИзәОұ»У‘Х“Зеію”Ј¬“ФЪОчІШЦ®Я…ҪзҶ–о}ҪвӣQЦ®З°Ј¬ЖдЛы—lҝоІ»ДЬұ»ҝј‘]”ЎЈўЩІўЦШУГТФЗ°РUҷMҗәБУјҝӮzНюГ{кҗЩO·¶Ј¬Из№ыІ»Н¬ТвУў·ҪТвТҠЈ¬УўҮшҫНҢўЦұҪУЕcОчІШХ„ЕРЎЈГжҢҰУў·ҪөДҸҠУІ‘B(tЁӨi)¶ИЈ¬кҗЩO·¶Пт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ХҲКҫЈ¬өГөҪөД…sКЗ“ПИЧhТІҹoІ»ҝЙ”Ўў“Ҫз„Х(wЁҙ)Чhә󣬑Ә(yЁ©ng)°ҙЦР·ҪМб°ёЦрТ»У‘Х“”өИНЧ…f(xiЁҰ)НЛЧҢөДҙрҸН(fЁҙ)ТвТҠЎЈН¬•rЈ¬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ЦёКҫБЛЧhҪзФӯ„tЈә“ПИЧhҙЁІШҪ»ҪзЈ¬ФЩХ“ЗаәЈЕcОчІШҪзҫҖЈ¬¶шҙЁІШҪ»Ҫз‘Ә(yЁ©ng)ФЪҪӯЯ_Ј¬ҪӯЯ_ТФ–|ҢЩҙЁЈ¬ТФОчҢЩІШЈ¬ЦРҮшЧоҙуЧҢІҪЦ»ДЬНЛЦБөӨЯ_ЎЈ”ўЪ“ю(jЁҙ)ҙЛФӯ„tЈ¬Ј¬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ЕcУўҙъұнј°ОчІШөШ·ҪҙъұнЯBАm(xЁҙ)ХЩй_·ЗХэКҪ•юЧhЙМХ„ОчІШҪз„Х(wЁҙ)Ҷ–о}ЎЈкҗЩO·¶ҸҠХ{(diЁӨo)ЦРҮшЕcОчІШөДҡvК·кP(guЁЎn)ПөЈ¬МбіцОчІШұҫҫНКЗЦРҮшҪ®УтөДТ»Іҝ·ЦЈ¬ТАҙЛФӯ„tЈ¬ЦРҮшҢҰҙЁІШҪзҫҖЧоҙуөДЧҢІҪКЗТФҪӯЯ_һй·ЦЛ®ҺXЈ¬ҪӯЯ_ТФОч„қИлОчІШЈ¬ө«ОчІШұШнҡЧрЦРҮшһй“ЧЪЦчҮш”ЎЈўЫПДФъҹoТ•ҡvК·КВҢҚЕc¬F(xiЁӨn)ҢҚЈ¬ИФТФөЪТ»ҙО•юЧhМбіцөДЦРІШҪ®ҪзһйңКЎЈлp·ҪҢҰУЪҪ®ҪзТӘЗуТАИ»‘ТКвЭ^ҙуЈ¬ҹo·ЁЯ_іЙИОәО…f(xiЁҰ)ЧhЎЈУў·Ҫ„tіГҷCМбіцЈ¬УЙ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ЕcОчІШөШ·ҪҙъұнёчЧФЛСјҜІДБПЈ¬ҝҳҢ‘•шГжХfГчЈ¬ФЪХэКҪ•юЧhЦРҪ»“QЈ¬УЙУў·Ҫ№«ХэСРЕРЎЈўЬ1914Дк1ФВ12ИХОчД·АӯөЪИэҙОХэКҪ•юЧhХЩй_Ј¬ЦчТӘУ‘Х“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ЕcОчІШөШ·ҪҫНҪз„Х(wЁҙ)Ҷ–о}ёчЧФМбіцөДТвТҠЎЈёщ“ю(jЁҙ)КВПИјs¶ЁЈ¬лp·ҪҙъұнҪ»“QБЛҫНҪз„Х(wЁҙ)Ҷ–о}ЛщңКӮдөДАнУЙЙкФV•шЈ¬ІўёчЛНыңҝЛсRәйТ»·Э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МбҪ»өДЎ¶кP(guЁЎn)УЪОчІШЯ…ҪзЦ®В•ГчЎ·Ј¬ёщ“ю(jЁҙ)ҡvК·ЙПЦРСлЕcёчөШұЈУРкP(guЁЎn)Пөј°ҮшлH·ЁЛщМбіцөД“УРР§ХјУР”Фӯ„tЈ¬МбіцТФҪрЙіҪӯһйҪзЎў“ЦРҮшХюё®ТӘЗуҪӯЯ_ј°ҪӯЯ_ТФ–|ёчөШ”өДАнУЙЈ¬ЦёіцҪӯЯ_ј°ҪӯЯ_ТФ–|ёчөШЈ¬ИзөВёсЎў°НМБЎўАнМБәНЛДҙЁІШ…^(qЁұ)өДЖдЛыҝhЈ¬ИэК®ҫЕЧеЎўЯ_Дҫј°ІмДҫ¶аәНІмУзЎўІЁГЬЎў°ЧсRҚҸөИөШТФј°ЗаәЈКЎөДІ»ЙЩөШ·ҪЈ¬ҪФТ»ЦұҡwУРкP(guЁЎn)КЎЦұҪУ№ЬЭ ЎЈўЭОчІШөШ·Ҫҙъұн„tНэСФОчІШФзГ“лxБЛЕcЦРҮшөДХюЦОкP(guЁЎn)ПөЈ¬МбіцТФйL‘cұ®ЧчһйОчІШҪзЦ·ЎЈЯ@ҙО•юЧhЛщУ‘Х“өДҪз„Х(wЁҙ)Ҷ–о}ұҫҒнКЗФЪУўҮшМбЧhПВЯMРРөДЈ¬ө«ыңҝЛсRәйҙЛ•r…sУЦА@й_ОчІШ“Ҫз„Х(wЁҙ)Ҷ–о}”Ј¬’ҒіцкP(guЁЎn)УЪОчІШХюЦОөШО»өД6ьcЦчҸҲЈ¬ЦШЙк1912Дк“8·17ӮдНьдӣ”ғИ(nЁЁi)ИЭЈ¬ІўҸҠЖИЦРҮшіРХJ“ОчІШУРНкИ«ЧФЦчҷа(quЁўn)Ј¬І»өГёДһйРРКЎ”Ј¬“ОчІШғИ(nЁЁi)Хю•әУЙУЎ¶ИХюё®ұO(jiЁЎn)¶Ҫ”Ј»І»ФКФSЦРҮшсvЬҠОчІШЈ¬¶ш“УўҮшөГсvұшУЪАӯЛ_”Ј¬“ЦРҮшЕcОчІШУРјҠ Һ•rЈ¬УЎ¶ИХюё®өГЕРӣQЦ®”өИЎЈўЮУўҮш№«И»ФҮҲDИЎҙъЦРҮшФЪОчІШөДЦчҷа(quЁўn)өШО»ЎЈ
2.“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”Ц®ХfЎЈЦұөҪ2ФВ17ИХОчД·АӯөЪЛДҙОХэКҪ•юЧhЙПЈ¬УўҮшІЕ’ҒіцЖдЛщЦ^өД“ҢҸІйТвТҠ”———Ў¶УўҮшХюё®кP(guЁЎn)УЪОчІШЯ…ҪзЦ®В•ГчЎ·Ј¬ІўёҪҳЛіцҪзПЮөДөШҲDТ»·ЭЎЈыңҝЛсRәйЯҖ·Ц„eУГ“Л{ҫҖ”әН“јtҫҖ”ҢўОчІШ·¶Үъ”MГыһй“ғИ(nЁЁi)ІШ”Еc“НвІШ”Ј¬ЧчһйҪвӣQҪз„Х(wЁҙ)Ҷ–о}өДЮk·ЁЎЈўЯЛщҳЛЛ{ҫҖһйЛщЦ^өД“ғИ(nЁЁi)ІШ”әН“НвІШ”өД·ЦҪзЈ¬јҙСШАҘҒцЙҪј№–|РРЈ¬Ҫӣ(jЁ©ng)ІсЯ_ДҫЕиөШДПҫүХЫПтДПҝзЯ^ҪрЙіҪӯәунҳһ‘ңжҪӯЕcҪрЙіҪӯ·ЦЛ®ҺXДППВЎЈЗаәЈҙуІҝЎў°НМБЎўАпМБЎўҙтјэ tөИөШҢЩУЪ“ғИ(nЁЁi)ІШ”Ј»АҘҒцЙҪТФДПЈ¬ҪрЙіҪӯТФОчұMҢЩ“НвІШ”ЎЈўаЛыХJһйЈ¬Я@ҳУҝЙТФ“ҙ_ұЈУўҮш°ўЛ_Д·ПІсRАӯСЕЙҪ…^(qЁұ)оI(lЁ«ng)НБөДИОәОТ»МҺІ»ФЩЕcғИ(nЁЁi)ОчІШЈ¬»тЦРҮш№ЬЭ Ц®ПВөДОчІШаҸҪУЈ¬ҫНҝЙТФ·АЦ№ЦРҮшИЛПтІҝВдЙҪөШқBНё”ЎЈўЩИз°ҙҙЛ°ёЈ¬ғИ(nЁЁi)өШөДҙуЖ¬өШ…^(qЁұ)ұ»„қҡw“ғИ(nЁЁi)ІШ”Ј¬¶шІэ¶јЎўІмУзЎўИэК®ҫЕЧеЎўЯ_ДҫөИөШ„қҪo“НвІШ”Ј¬ёьһйЦШТӘөДКЗЦРҮшЯҖҢўК§ИҘФЪ“НвІШ”өДТ»ЗРҷа(quЁўn)АыЎЈ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ХJһйУўҮшҙЛЕeНкИ«·ВР§БЛ¶нҮш№П·ЦГЙ№ЕөДјҝӮzЈ¬°СОчІШЦ«Ҫвһй“ғИ(nЁЁi)ІШ”Еc“НвІШ”Ј¬ЖуҲDҢўЛщЦ^өД“НвІШ”ҸДЦРҮш·ЦБСіцИҘЈ¬ЦГУЪУўҮшөДҝШЦЖЦ®ПВЈ¬УГ“НвІШ”ЧФЦОЦ®ГыЈ¬РРОчІШ“ӘҡБў”Ц®ҢҚЎЈТтҙЛЈ¬ЦРҮшНвҪ»ІҝлҠБокҗЩO·¶ПтУўҮшМбіцсgҸН(fЁҙ)ТвТҠЈәТ»КЗІ»ДЬТФҡvК·ЙПЦРҮшёчГсЧеЛщҪЁНхіҜһйҪсИХ„қҪзЦ®ТА“ю(jЁҙ)Ј¬ІўМШ„eВ•Гч“ҹoҷа(quЁўn)ёоЧҢИОәОҸДЗ°ЗеХюё®А^іРЦ®оI(lЁ«ng)НБЈ¬О©УРТ»ИзјИНщөШұЈИ«оI(lЁ«ng)НБ”Ј»¶юКЗУўҮшЛщМбіцөД“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”ЕcЦРҮшҡvҒнҢҰОчІШј°ЖдЛыІШ…^(qЁұ)өД№ЬЭ ЗйӣrёщұҫІ»·ыЈ¬ыңҝЛсRәйөД“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”ТІҸДОҙіц¬F(xiЁӨn)ФЪ№ЕҪсЦРНвИОәО№«й_УӣдӣәН№Щ·ҪОДјюЦ®ЦРЎЈўЪ
3.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ЎЈкҗЩO·¶ТАХХ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ЦёБоҢҰУўҮшМбіцөДЎ¶УўҮшХюё®кP(guЁЎn)УЪОчІШЯ…ҪзЦ®В•ГчЎ·ј°“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”Ц®ХfЯMРРсgҸН(fЁҙ)әуЈ¬УўҮшІЯ„УОчІШөШ·Ҫ·ЦБС„ЭБҰПтҙЁЯ…ЯMРРЬҠКВЯM№ҘЈ¬ФҮҲDФміЙ“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”„қ·ЦөДјИіЙКВҢҚЎЈН¬•rЈ¬Уў·ҪУЦЕcПДФъГЬЗРЕдәП№«й_ФмЦ{Јә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ЬҠ“ҸДАӯЛ_ТФДПәНТФұұН¬•rҢҰІШИЛ°l(fЁЎ)„УЯM№Ҙ”Ј¬ЯBАm(xЁҙ)¶аҙО“Тu“ф”Ўў“ЕЪЮZ”ЛщЦ^өДОчІШ“Я…·АЬҠ”Ј¬ҡўЛАОчІШ“Я…·АЬҠ”ёЯ№ЩҸҠ°НөИИЛЈ¬“ҹэҡ§ФS¶а·ҝОЭөИ”ЎЈўЫыңҝЛсRәйІўТФ“ҙЁІШ‘р(zhЁӨn)КВ‘ОЈјұ’Ј¬ИОәОҮАЦШӣ_Н»¶ј•юК№ёч·ҪТФј°ЖдХюё®ё¶іціБЦШҙъғr”һйУЙТӘЗујУҝмХ„ЕРЯMіМЈ¬ўЬІўАыУГЦ{СФ№Ҙ“фГсҮшЦРСлХюё®“І»КШРЕУГ”Ј¬һйОчІШөШ·Ҫ·ЦБС„ЭБҰЯMРРөД·ЦБС»о„УЦЖФмҪиҝЪЈ¬һйЖд’ҒіцөД“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”Ц®ХfҙуФмЭӣХ“ЎЈФЪЯ@·NЗйРОПВЈ¬3ФВ11ИХОчД·АӯөЪОеҙОХэКҪ•юЧhХЩй_ЎЈУўҮшҙъұнТАЕfҪиҝЪҙЁІШ‘р(zhЁӨn)КВ“ОЈјұ”Ј¬ІўТФ°СОчІШөШ·ҪЧчһйН¬өИҮшјТҢҰҙэөДҝЪОЗХf“ИэҮшАыТж¶ј ҝЙжЖдЦР”Ј¬“әфУхЦРІШҢЈҶTҫoјұРР„УТФҢӨЗуҶ–о}Ц®ҪвӣQ·Ҫ°ё”Ј¬ИзИфНПСУЈ¬“ҝЙДЬ•юҢ§(dЁЈo)ЦВТ»·NҮАЦШНюГ{ИэҮшХюё®АыТж”өДҫЦГжЈ¬ўЭІў’ҒіцБЛ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11—lј°Жд“ёҪҝо”6—lЎЈЖдғИ(nЁЁi)ИЭ»щұҫЦШҸН(fЁҙ)БЛУўҮшХюё®Ц®З°ПтЦРҮшХюё®МбіцөДкP(guЁЎn)УЪОчІШҶ–о}өД·Ҫ°ёәНХХ•юөДғИ(nЁЁi)ИЭЈ¬ТФј°НэҲDҢўОчІШҸДЦРҮш·ЦБСіцИҘөД·З·ЁТӘЗуЎЈыңҝЛсRәйЯҖНюГ{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ХfЈ¬Я@КЗҢҰЦРҮшөДЧоҙуЧҢІҪЈ¬Из№ыЦР·ҪІ»Н¬ТвЈ¬®”ҝј‘]Т»ЗРҮАЦШөДәу№ыЎЈ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ёщұҫҫНКЗЕЕіэЦРҮшФЪОчІШөДЦчҷа(quЁўn)өШО»Ј¬ІўФцјУУўҮш«@өГөД·N·NМШҷа(quЁўn)Ј¬ЖдҢҚЩ|(zhЁ¬)ИФКЗҢҚК©әННЖРРУўҮш1912ДкМбіцөД“8·17ӮдНьдӣ”ЗЦІШРВВФЎЈ
кҗЩO·¶®”ҲцҢҰУў·ҪЯMРРсgівЈ¬ХJһйёч·ҪҢҰЦШҙуҶ–о}ЙРОҙЯ_іЙТ»ЦВФӯ„tТвТҠЈ¬ҙЛ•rМбіц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·ЗіЈІЭВКЎЈыңҝЛсRәй„tҸҠБТ·ҙҢҰЈ¬ІўңКӮдЖрІЭ…f(xiЁҰ)ЧhТФјУҝмХ„ЕРЯMіМЈ¬¶шЗТ…f(xiЁҰ)ЧhІЭ°ёЯҖТӘТФ2ФВ17ИХөЪЛДҙОХэКҪ•юЧhЙПЛщМбіцөДТ»°гФӯ„tһй»щөA(chЁі)ЎЈПДФъ·eҳOН¬ТвУў·ҪМбЧhЈ¬ҙр‘Ә(yЁ©ng)ҢҰУў·Ҫ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ід·Цҝј‘]ЎЈФЪҙЛЗйҫ°ПВЈ¬кҗЩO·¶ТІЙоёРҹoДОЈ¬Ц»әГҢў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іКЛН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ЎЈҙЛНвЈ¬ФЪЯ@ҙО•юЧhЗ°әуЈ¬ЦРҮшНвҪ»Іҝ№ЩҶTоҷҫSвxФш¶аҙО•юТҠЦм –өдЈ¬ұнКҫЗаәЈ®”ҢЩЦРҮш№ЬЭ Ј»ҙЁІШҫҖЕӯҪӯТФ–|ҡw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ЦОАнЈ¬ТФОчЦБҪӯЯ_Т»Һ§Ј¬ҝЙФКФSұЈіЦЕfЦЖІ»ФO(shЁЁ)ҝӨҝhЎЈкҗЩO·¶ФЪ·ЦОц®”•rРО„ЭәуЈ¬ТІ¶аҙОПт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ХҲКҫЧоәуЧҢІҪТвТҠЎЈУў·ҪЧФТФһйУўІШГШГЬ•юЧhЯ_іЙөДЛщЦ^өД“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”·Ҫ°ёҝЙТФҢҚ¬F(xiЁӨn)Ј¬І»ҪУКЬ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өДЧҢ
ІҪТвТҠЈ¬ІўНюГ{ЦРҮшИфҲФіЦЧФјәөДТвТҠЈ¬„t“ұШҢў°l(fЁЎ)ЙъЦШҙукP(guЁЎn)Пө”ЎЈУЦФЪ3ФВ26ИХ(3ФВ
25ИХУўІШЯ_іЙГШГЬ…f(xiЁҰ)ЧhўЩ)№«й_НюГ{кҗЩO·¶Ј¬ИзИфҫЬҪ^У‘Х“Уў·ҪМбіцөД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Ј¬Уў·ҪҢўҶОӘҡЕcОчІШ•юХ„Ј¬ІўҢўУўІШ…f(xiЁҰ)ЧhІЭ°ёЛНҪ»Я_ЩҮА®ВпЕъңКЎЈ
4.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өДсgівј°НЧ…f(xiЁҰ)ЎЈҙЛ•rФ¬КА„PИОҙуҝӮҪy(tЁҜng)өД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ХэЕcДП·ҪУ‘Ф¬ҙуЬҠЧч‘р(zhЁӨn)Ј¬јұРиУўҮшЦ§іЦЈ¬ТтҙЛҢҰУЪУў·ҪМбіцөД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ЧцБЛәЬҙуЧҢІҪЈ¬ЦБОчД·АӯөЪБщҙОХэКҪ•юЧhХЩй_З°Т»ЯBЧцБЛИэҙОЧҢІҪЈ¬ЧоәуЙхЦБМбіц“ТФөӨЯ_һйҪзЈ¬ЕӯҪӯТФОчЦБөӨЯ_І»ёДЕfЦЖЈ¬І»ФO(shЁЁ)ЦЭҝh”ЎЈФЪ4ФВ7ИХХЩй_өДөЪБщҙОХэКҪ•юЧhЙПЈ¬кҗЩO·¶ЧсНвҪ»ІҝЦёБоаҚЦШ°l(fЁЎ)ұнВ•ГчЈ¬ЦШЙкБЛЦРҮшХюё®ЧоәуөДЧҢІҪТвТҠЎЈПДФъҫ№ТФІЎһйУЙЧҢУў·ҪҙъұныңҝЛсRәйөДЦъКЦШҗ –ҙъМжЧФјә…ў•юЈ¬кҗЩO·¶ҢҰҙЛҫ№И»НЛЧҢЯwҫНЈ¬ӣ]УРМбіц·ҙҢҰТвТҠЎЈ4ФВ15ИХЈ¬ыңҝЛсRәйЦъКЦҠдҺҹУЦЕcкҗЩO·¶ҢҰ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ЯMРР“ҙиЙМ”Ј¬кҗЩO·¶ід·ЦкUКцБЛЦРҮшХюё®өДТвТҠЈәҸҠБТ·ҙҢҰ“ҢўОТОчІШөШ·ҪЧчһйПнУРЦчҷа(quЁўn)өДЎўӘҡБўөД‘ҮшјТ’Ј¬ҪoУиОчІШТФЕcЦРҮшЎўУўҮшЖҪөИөДөШО»”Ј»ұШнҡ„hіэ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ЦРЛщУРкP(guЁЎn)УЪЦРҮшҢҰОчІШ“ҹoЦчҷа(quЁўn)”Ўў“ЦіГсХЯ”өИХZСФЈ¬ұШнҡ“ФцјУТ»—lҝоіРХJОчІШКЗЦРҮшөДТ»Іҝ·Ц”Ј»‘Ә(yЁ©ng)ҙ_Бў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сvІШйL№ЩФЪОчІШҢҰНвКВ„Х(wЁҙ)ЦРөДЦёҢ§(dЁЈo)өШО»Ј»РЮёД“НЁЙМХВіМ”Ҫ^ҢҰІ»ДЬ“pәҰЦРҮшФЪОчІШөДЦчҷа(quЁўn)өШО»Ј»ҲФӣQ“нЧoЦРСлФЪОчІШәНЛДҙЁЎўЗаәЈЎўёКГCЎўФЖДПЛДКЎІШ…^(qЁұ)өД№ЬЭ ҷа(quЁўn)Ј»ҲФӣQ·ҙҢҰ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ЦРЛщЦ^ҢҰОчІШ“Щrғ””өДғИ(nЁЁi)ИЭј°УўҮшҢҰЦРҮшОчІШөШ·ҪКВ„Х(wЁҙ)өДёЙЙжЈ¬ҲФӣQҫSЧoЦРҮшФЪОчІШөДЦчҷа(quЁўn)ЎЈУў·Ҫ„tҢҰЦР·ҪМбіцөДРЮёДТвТҠІ»Уиҝј‘]Ј¬В•·QІ»•юФЩЧцЯMТ»ІҪЧҢІҪЈ¬Ц»ДЬ°ҙХХУў·ҪТвТҠЎЈҙЛәуЈ¬ыңҝЛсRәйУЦЕcкҗЩO·¶ЯMРР•юНв“ҙиЙМ”Ј¬ҫНЛщМбІЭјsЯMРРРЮёДЎЈө«ҸДРЮёДөДғИ(nЁЁi)ИЭҝҙЈ¬УўҮшИФИ»ҲФіЦФӯҒнЦчҸҲЈ¬ҫЬІ»ЧҢІҪЎЈ4ФВ20ИХЈ¬ЦРҮшНвҪ»ІҝлҠБокҗЩO·¶‘Ә(yЁ©ng)БҰ ҺҲФіЦәНҫSЧoҮшјТЦчҷа(quЁўn)Ј¬ө«Н¬•rТІМбіц“ФЩЗъСӯУўИЛЦ®ТвЈ¬ФКЧҢ‘ғИ(nЁЁi)ЎўНвІШ’ГыДҝ”Ј¬ПтУўҮшЧцБЛөЪОеҙОЧҢІҪЈ¬”MТФ®”АӯҺXТФұұЗаәЈФӯҪзј°°ў¶ШјҜЎў°НМБЎўАнМБёчөШИФХХЦРҮшғИ(nЁЁi)өШЦОАнЈ¬ЕӯҪӯТФ–|ј°өВёсЎўХ°ҢҰЎўІмДҫ¶аЎўИэК®ҫЕЧеёчөШЈ¬ИФСШҝҰДҫГы·Q¶ЁһйМШ„e…^(qЁұ)Ј»ЕӯҪӯТФОч„қҡwОчІШЧФЦО·¶ҮъЈ¬О©кP(guЁЎn)УЪХюЦОЎўНБөШҪ»ЙжҶ–о}Ј¬УЙЦРУў…f(xiЁҰ)ЙМЈ¬ІўңКІШИЛ…ўЕcЎЈўЪ
5.ІЭәһ—lјsЎЈГсҮшЦРСлҙъұнЕcГсҮшЦРСлХюё®»ҘЦВөДлҠҲуұ»ыңҝЛсRәйҪШ«@Ј¬ыңҝЛсRәйФЪөГЦӘЦРҮшХюё®‘B(tЁӨi)¶ИәуЈ¬ёДЧғІЯВФЈ¬ҙ®НЁПДФъМбіцБўјҙЕeРРөЪЖЯҙОХэКҪ•юЧhІЭәһУў·ҪЛщМбіцөД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ЎЈФЪ4ФВ22ИХЕeРРөДІЭәһ•юЧhЙПЈ¬Уў·ҪЕcПДФъТ»іӘТ»әПЈ¬ГЬЗРЕдәПЎЈыңҝЛсRәйПИҢўЖдЛщРЮёДөД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ј°ЛщёҪөШҲD·ЕФЪЧАЙПЈ¬ұЖҶ–кҗЩO·¶“Лщ”MјsёеҝЙФКРР·с”ЈҝкҗЩO·¶ёщ“ю(jЁҙ)ЦРҮшНвҪ»Іҝ20ИХВ•ГчЦёіцҙЛјsёеЙРОҙЯ_іЙ…f(xiЁҰ)ЧhЈ¬І»‘Ә(yЁ©ng)ҝј‘]ІЭәһҶ–о}ЎЈыңҝЛсRәйЯҖЯ…ҪвбҢХfҪУөҪ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лҠҲуЭ^НнЈ¬І»ДЬј°•rӮчҪoОчІШөШ·ҪҙъұнФ”јҡСРҫҝЈ»УЦХf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өДТӘЗу“НкИ«Я`ұіІЭ”M…f(xiЁҰ)ЧhөДТ»°гФӯ„t”Ј¬КЗ“І»оҷТФЗ°У‘Х“өДҪY(jiЁҰ)№ыТФј°ЛыӮғЛщМбҪ»өДЧC“ю(jЁҙ)”Ј¬ұнКҫІ»ДЬҪУКЬЈ¬ТӘЗуА^Аm(xЁҙ)У‘Х““…f(xiЁҰ)ЧhІЭ°ё”өДәһЧЦҶ–о}Ј¬кҗЩO·¶ҲФӣQВ•ГчІ»ДЬІЭәһЎЈПДФъ…sЕдәПУў·Ҫ№КТвХfЈ¬ИфГсҮшЦРСлҙъұнІ»Н¬ТвІЭәһјsёеЈ¬ОчІШөШ·ҪҢў·ҙҢҰ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ЦРУРкP(guЁЎn)уw¬F(xiЁӨn)ЦРҮшФЪІШЦчҷа(quЁўn)өД—lОДЎЈТҠҙЛЗйҫ°Ј¬ыңҝЛсRәйУЦЕдәПОчІШөШ·ҪҙъұнХfЈ¬“Я@ҙО•юЧhұҫҒнҫНКЗЧоәуҪY(jiЁҰ)Х“РФөД•юЧhЈ¬ө«ФЪЦРҮшҢЈҶTөДТӘЗуПВТСНЖЯtҺЧМм”Ј¬Іў№КТвНюГ{ХfЈ¬•юЧhТСәД•r°лДкЈ¬јҜёч·ҪТвТҠіЙҙЛјsёеЈ¬ДгӮғ?nЁЁi)фІ»қMТвЈ¬Ц»өГҢўјsёеИЎПыЎЈкҗЩO·¶мoУ^ЖдЧғЈ¬ӣ]УР»Ш‘Ә(yЁ©ng)Ј¬•юЧhПЭУЪҢАЮОҫЦГжЈ¬ЦВК№Уў·Ҫҹo·ЁКХҲцЎЈЧоәуЈ¬ыңҝЛсRәйУЦІ»өГІ»ЧФХТЕ_лAХfКЗ“ҙЛКВкP(guЁЎn)ПөЦШҙуЈ¬ФёҢўҙЛҙО•юЧhСУйLТ»ИХЈ¬УЪГчИХТФФКЎў·с¶юЧЦТҠҸН(fЁҙ)ЎЈЦБ?xЁӘ)rИфИФұЛҙЛҪ©іЦЈ¬„tУў·ҪЦ®јsёејҙі·»Ш”ЎЈҢҰҙЛЧоәуНЁләЈ¬кҗЩO·¶ұнКҫ·ҙҢҰХfЈ¬БўјҙҙрТФ“ФКЎў·с¶юЧЦЈ¬ұҫҶTҹoҷа(quЁўn)ЙГ¶Ё”Ј¬ІўҲФіЦСУЖЪЛДМмЈ¬ТФҢў•юЧhЗйРОлҠіК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ӣQ¶ЁЎЈУў·ҪГгһйҙр‘Ә(yЁ©ng)ЦБ27ИХЙПОзһйЦ№ЎЈўЩ22ИХЈ¬кҗЩO·¶ХҲКҫЦРСлЈ¬ЦРҮшНвҪ»ІҝФЪҪУөҪХҲКҫәулҠёжсvУў№«К№„ўУсчлТӘЗуЖдҫНҙЛКВЕcУўҮшНвҪ»ІҝЯMРРЗРҢҚҙиЙМЈ¬ІўГчҙ_ЦёКҫЈ¬ҙЛЗ°ЧҢІҪТСһйЦРҮшХюё®ЧоәуЧҢІҪЈ¬ИфУў·ҪҢҰЦР·ҪТвТҠИФІ»УиТФҝј‘]Ј¬„tҢўҒнХ„ЕРЖЖБСЈ¬ЦРҮшХюё®ЧФІ»Ш“ИОәОШҹ(zЁҰ)ИОЎЈ23ИХЈ¬„ўУсчл»ШлҠ“УўНвҪ»ІҝҫЬҪ^ЦРҮшХюё®ҝ№Чh”ЎЈ25ИХЈ¬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ҸН(fЁҙ)лҠкҗЩO·¶“Уў·ҪЧФТа‘Ә(yЁ©ng)МбіцЧҢІҪЈ¬КјҝЙҢҰІШКВА^Аm(xЁҙ)ЯMРРУСЙЖХ„ЕРөИ”Ј¬ө«ҢҰ“Х{(diЁӨo)НЈјsёе”КЗҫЬКЗәһӣ]УРГчКҫЎЈ27ИХЙПОзөЪБщҙОХэКҪ•юЧhҸН(fЁҙ)•юЈ¬ыңҝЛсRәйИФҲФіЦ22ИХТвТҠЈ¬Іў·Q“ДҝЗ°өДФӯ„tІ»ДЬУРИОәОёД„У”Ј¬ЧоәуХf“ЙМЧh•rЖЪ¬F(xiЁӨn)ТСЯ^ИҘЈ¬ҪсО©УыФғЩFҢЈҶTФК·с®ӢРР¶шТС”ЎЈкҗЩO·¶ұнКҫ“Оҙ·оХюё®У–(xЁҙn)БоЈ¬І»ДЬ®ӢРР”Ј¬ҫЬҪ^әһЧЦЎЈыңҝЛсRәйҫ№РUҷMТӘЗукҗЩO·¶лxй_•юҲцЎЈкҗЩO·¶НЛҲцәуЈ¬ыңҝЛсRәйЕcПДФъ№ІН¬ЙМЧhҢҰё¶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өДЮk·ЁЈ¬ЛыТӘЗуПДФъН¬ТвҢҰХ{(diЁӨo)НЈјsёеЙФЧчР©“І»•юҢҰОчІШІ»АыөДёД„У”Ј¬ФҮҲDУГЧцТ»Р©ЧҢІҪөД·ҪКҪТэХTкҗЩO·¶әһЧЦЈ¬ПДФъұнКҫН¬ТвЎЈәуЈ¬Уў·ҪЕcОчІШөШ·ҪҙъұнҮАЦШЯ`ұіҮшлH·ЁФӯ„tәНҮшлH‘TАэЈ¬ҫ№И»ФЪ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лxПҜөДЗйӣrПВЈ¬ФЪІЭјsј°ёҪҲDЙПЯMРРБЛәһЧЦЎЈ¶шФЪБнТ»·ҝйgЈ¬Уў·ҪҠдҺҹТІГчҙ_ёжФVкҗЩO·¶ЈәУў·ҪТСЕc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ЙМНЧЈ¬ІўҢўјsёе®ӢРРЈ¬Из№ыкҗЩO·¶І»®ӢРРЈ¬УўҮшјҙЕcОчІШУҶјsЈ¬І»ФЩЕcкҗЩO·¶ЙМЧhЎЈІўЯMТ»ІҪТэХTкҗЩO·¶Ј¬ІЭәһІў·ЗҫҶҪY(jiЁҰ)ёч·ҪЦ®ТвЈ¬јsёеІЭәһәуЈ¬ЙРРиҪӣ(jЁ©ng)Я^ХэКҪәһЧЦј°ҫҶҪY(jiЁҰ)ёч·ҪЦ®ХэКҪЧCҢҚј°ЕъңККјһйУРР§Ј»ІЭәһјsёеәуЈ¬ИзЦРҮшЦРСлХюё®І»Н¬ТвЈ¬ИФҝЙҫЬҪ^әһЧЦЈ¬јsёеҹoР§ЎЈЧоәуНюұЖкҗЩO·¶Јәө«ИфҪсИХІ»ІЭәһЈ¬„tХ„ЕРБўјҙЖЖБСЎЈҙЛ•rкҗЩO·¶ТСЯMНЛғЙлyЈ¬Т»·ҪГжІ»ДЬЯ`ұіЦРСлХюё®өДЦёБоЈ¬БнТ»·ҪГжТІіР“ъ(dЁЎn)І»БЛУўІШЦұҪУәһјsөДШҹ(zЁҰ)ИОЎЈЧоәуЈ¬ТтІ»Фё“ъ(dЁЎn)Ш“ОчД·Аӯ•юЧhТтЛыҫЬҪ^®ӢСә¶шЦР”аөДШҹ(zЁҰ)ИОЈ¬кҗЩO·¶ӣQ¶ЁҸДҷа(quЁўn)ІЭәһ—lјsЈ¬ө«аҚЦШВ•ГчЈә“®ӢРРЕcәһСә®”·ЦһйғЙКВЎЈ®ӢРРДЛҢЈҶTТ»•rҷа(quЁўn)ТЛЦ®ЕeЈ¬ө«Хюё®ИфІ»ЕъңКЈ¬јҙІ»ДЬ°l(fЁЎ)ЙъР§БҰЈ¬әһСә„t·ЗөГХюё®У–(xЁҙn)БоЈ¬ИfІ»ДЬХХЮkЎЈУўҢЈҶT®”һйТ»Т»ФКЦZЎЈ”ўЪыңҝЛсRәйұнКҫН¬ТвЎЈкҗЩO·¶ІЭәһөДПыПўұ»ЕыВ¶әуЈ¬И«ҮшЭӣХ“ҮWИ»Ј¬ҢҰУў·ҪІЯ„қ·ЦБСОчІШөДкҺЦ\ұнКҫҸҠБТҝ№ЧhЈ¬ҢҰОчІШөШ·ҪУHУў·ЦЧУұіЕСЧжҮшөДРРһйҳOһй‘Қҝ®Ј¬ҢҰГсҮшЦРСлҙъұнөДІЭәһРРһйұнКҫҸҠБТ·ҙҢҰЎЈ
ЛДЎў“ОчД·АӯІЭјs”Еc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өДҹoР§РФ
—lјsКЗҮшлH·ЁЦчуwФO(shЁЁ)¶Ёлp·ҪөДҷа(quЁўn)АыЕcБx„Х(wЁҙ)Ј¬ТтҙЛұШнҡУРҫҶјs·ҪөДәПТвІЕДЬЯ_іЙТ»ЦВөД…f(xiЁҰ)ЧhРОіЙ—lјsЎЈЎ¶ҫSТІј{—lјs·Ё№«јsЎ·өЪ39—lГчҙ_ТҺ(guЁ©)¶ЁЈә“—lјsөГНЁЯ^Ждёч®”КВҮшЦ®йgөД…f(xiЁҰ)¶ЁЈ¬УиТФРЮХэ”Ј¬ўЩЯ@КЗ“—lјsұШнҡЧсКШФӯ„t”әНҮшјТЦчҷа(quЁўn)Фӯ„tөДТӘЗуЈ¬ТІКЗ®”•rөДҮшлH·ЁТҺ(guЁ©)„tөДуw¬F(xiЁӨn)ЎЈЯ@ҫНТӘЗуҫҶјs·ҪФЪ»ҘПа…f(xiЁҰ)ЙМЦРЯ_іЙТ»ЦВЈ¬¶шІ»ДЬТ»·Ҫ(»тҺЧ·Ҫ…f(xiЁҰ)Н¬)Г{ЖИЎўЖЫт_БнТ»·Ҫ(»тҺЧ·Ҫ)Ј¬·с„tұг®a(chЁЈn)ЙъПа‘Ә(yЁ©ng)өДҮшлH·Ёәу№ыЎЈ
1.ҮшјТ„қҪзФӯ„tЎЈёщ“ю(jЁҙ)ҮшлHҢҚЫ`‘TАэЈ¬„қҪзНЁіЈРиҪӣ(jЁ©ng)Я^¶ЁҪзәНҳЛҪзғЙӮҖЯ^іМЎЈКЧПИКЗҫҶјsҮшНЁЯ^…f(xiЁҰ)ЙМЎўХ„ЕРәуәһУҶТ»ӮҖЯ…Ҫз—lјsҙ_¶ЁЯ…ҪзөДЦчТӘО»ЦГәН»щұҫЧЯПтЈ»И»әуҫҶјsҮшИОГьёчЧФҙъұнҪMіЙ„қҪзОҜҶT•юЈ¬ЯMРРҢҚөШҝұІмЈ¬ҸД¶шҙ_¶ЁЯ…ҪзҫҖөДҫЯуwО»ЦГЈ¬ІўЗТҳдБўҪзұ®»тҪзҳ¶ЧчһйҮшјТЯ…ҪзҳЛЦҫЎЈДбИХАыҒҶҮшлH·ЁҢW(xuЁҰ)јТA·O·ҝЁҝЛһхАӯәХХJһйЈә“Из№ыДіТ»ҮшјТЦшКЦҝұІмІўФҮҲDФЪЧФјәЯ…ҪзөШ…^(qЁұ)„қҪзЈ¬¶шаҸҪьБнТ»ӮҖУРЦұҪУАыәҰкP(guЁЎn)ПөөДҮшјТФЪЖдҢҚК©ЦРӣ]УРҪoУиИОәОәПЧч»тХЯН¬ТвҪУКЬЖд„қҪзҪY(jiЁҰ)№ыЈ¬ҸДЛҫ·ЁФӯ„tҒнЦvҙЛ·NҶО·ҪГжөДРРһйҢҰБнТ»·ҪҮшјТҹoР§Ј¬ҮшлHЯ…ҪзТАИ»ӣ]УР„қ¶ЁЎЈ”ўЪФЪОчД·Аӯ•юЧhЦРЈ¬ыңҝЛсRәйёщұҫҫНӣ]УРЕc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ҙъұнУ‘Х“Ј¬…sТФШҗ –өД·З·ЁҝұІмЩYБПһйТА“ю(jЁҙ)Ј¬ҶО·ҪФЪ“ұИАэіЯһйТ»УўҙзөИУЪ°ЛУўАпөДөШҲDЙП”®Ӣіц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Ј¬ІўИыЯMБЛёҪҲDЈ¬НкИ«КЗыңҝЛсRәйөДҶО·ҪРРһйЈ¬п@И»Я`ұіБЛҮшлH·ЁЦРҫҶјsҮш„қҪзФӯ„tЎЈ
2.—lјsІЭәһР§БҰЎЈ—lјsІЭәһУЙҫҶјsҮшХ„ЕРҙъұнФЪ—lјsІЭ°ёЙПәһГыЈ¬ұнКҫХ„ЕРҙъұнҢҰ—lјsІЭ°ёөДХJН¬ЎЈТ»°гҒнХf“ІЭәһәН•әәһІ»КЗХэКҪәһКрЈ¬І»ҫЯУРХэКҪәһКрөДР§БҰЈ¬¶јКЗөИҙэХэКҪәһКрөДТ»ӮҖІҪуE”ЎЈўЫҫҶјsҮшХюё®КЪҷа(quЁўn)әһЧЦөДГьБоөҪЯ_әуҪӣ(jЁ©ng)Я^ХэКҪәһЧЦЈ¬—lјsІЕДЬЙъР§ЎЈУўҮшҮшлH·ЁҢЈјТыңҝЛДО –ХJһйЈәІЭәһІўІ»өИУЪХэКҪәһЧЦЈ¬Ц»КЗ“®”Х„ЕРҪY(jiЁҰ)КшәН—lјsәһКрЦ®йgПаёфТ»ӮҖ•rЖЪ•rЈ¬И«ҷа(quЁўn)ҙъұн°СІЭәһёҪУЪ—lјsЦ®әуЈ¬ҒнұЈЧCјsОДөДҙ_ҢҚ”ЎЈўЬФЪОчД·Аӯ•юЧhЙПЈ¬кҗЩO·¶ЖИУЪүәБҰәНУў·ҪНюГ{Ј¬ІЭәһБЛ—lјsЈ¬ө«Я@ғHғHұнКҫХJЧCјsОДЈ¬І»ҫЯУР—lјs·ЁЙПөДР§БҰЎЈ®”•rкҗЩO·¶ФЪІЭәһЗ°ТСҪӣ(jЁ©ng)В•ГчЈ¬®ӢРРЕcәһСәһйғЙјюКВЗйЈ¬®ӢРРКЗЖдТ»•rЦ®ЕeЈ¬ИзГсҮшЦРСлХюё®І»ЕъңКЈ¬І»ДЬ°l(fЁЎ)ЙъР§БҰЎЈкҗЩO·¶өДВ•ГчТІөГөҪБЛыңҝЛсRәйөДХJН¬Ј¬ТтҙЛкҗЩO·¶ІЕ“ОҙәтЦРСлГьБоЈ¬ЙГЧФ®ӢРР”ЎЈЎ¶ОчД·Аӯ—lјsЎ·ј°ЖдЛщ®a(chЁЈn)ЙъөД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ұШнҡҪӣ(jЁ©ng)Я^ЦРҮшЦРСлХюё®өДЕъңКІЕДЬЙъР§ЎЈКВҢҚЙПЈ¬ЦРҮшҫЬҪ^ХэКҪәһЧЦЈ¬ёьӣ]УРЕъңКЈ¬ТтҙЛЎ¶ОчД·Аӯ—lјsЎ·Еc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І»ҫЯУРәП·ЁРФЎЈ
3.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ҮАХэВ•ГчөДР§БҰЎЈёщ“ю(jЁҙ)ҮшлH·ЁТ»°гФӯ„tЈ¬Йжј°Я…ҪзөД—lјsјҙК№ТСәһКрЯҖұШнҡҪӣ(jЁ©ng)Я^ҮшғИ(nЁЁi)Бў·ЁҷCкP(guЁЎn)(»тЦРСлХюё®)өДЕъңКЎЈҢҰУЪәһКрәуРијУЕъңКөД—lјs“ФЪЛГәуЕъңК—lјsЦ®З°Ј¬ҮшјТКЬҫРКшөДН¬ТвҢўІ»КЗУРР§өД”ЎЈўЭөВҮшҢW(xuЁҰ)ХЯУўёк·сT·йhПЈТІХJһйЈә“Чh¶ЁәНәһКр—lјsјsОДЈ¬—lјsЙРОҙҫЯУРјsКшБҰЎЈ”ўЮГсҮшЦРСлХюё®4ФВ28ИХҪУөҪкҗөДлҠҲуәуЈ¬УЪ29ИХБўјҙҸН(fЁҙ)лҠЈә“ҲМ(zhЁӘ)КВКЬЖИ®ӢРР”Ј¬Хюё®І»ДЬіРХJЈ¬‘Ә(yЁ©ng)јҙВ•ГчИЎПыЎЈўЩкҗЩO·¶јҙҝМТАБоВ•ГчИЎПыЎЈЦРҮшНвҪ»Іҝ30ИХХЩТҠЦм –өдЈ¬ҸҠБТҝ№ЧhУў·ҪРРһйЈ¬ІўХэКҪРРОДВ•ГчкҗЩO·¶өДІЭәһОҙ·оХюё®У–(xЁҙn)БоЈ¬ДЛКЗӮҖИЛІ»ХэКҪЦ®®ӢРРЈ¬ЦРҮшЦРСлХюё®ТСјҙҝМлҠБоИЎПыЈ¬ІўЦШЙкЦРҮшІ»Н¬ТвУўҮшЛщМбөД—lјsІЭ°ёЎЈ5ФВ1ИХЈ¬ЦРҮшсvУў№«К№„ўУсчлПтУўНвҪ»ҙуіјҫНЙПКцКВјюМбіцҝ№ЧhЈ¬ІўЦШЙкБЛГсҮшЦРСлХюё®В•ГчЎЈкҗЩO·¶ТІёщ“ю(jЁҙ)ГсҮшЦРСлХюё®өДЦёБоЈ¬В•ГчЦРҮшХюё®өД·ҙҢҰТвТҠЈ¬ҫЬҪ^ФЪ—lјsЙПХэКҪәһЧЦЎЈһйБЛ·АЦ№Уў·ҪҙъұнәНОчІШөШ·ҪҙъұнЦЖФмкҺЦ\Ј¬кҗЩO·¶ҙъұнЦРҮшХюё®УЦаҚЦШВ•ГчЈә·ІУўҮшәНОчІШЛщәһ—lјs»тоҗЛЖОДјюЈ¬ЦРҮшХюё®Т»ёЕІ»УиіРХJЎЈЦРҮшсvУў№«К№„ўУсчлТІ·оГьХХ•юУўҮшХюё®ЦШЙкЦРҮшХюё®В•ГчЎЈўЪ
4.ОчІШөШ·ҪІ»ҫЯӮдҫҶҪY(jiЁҰ)—lјsЦчуwЩYёсЎЈҮшлH·ЁӮчҪy(tЁҜng)АнХ“ХJһйҮшјТКЗОЁТ»өДҮшлH·ЁЦчуwЈ¬—lјsТІТ»°гЦ»ДЬФЪҮшјТйgҫҶҪY(jiЁҰ)КЗҮшлHөДНЁіЈЧц·ЁЎЈЎ¶ҫSТІј{—lјs·Ё№«јsЎ·өЪ46—lТҺ(guЁ©)¶ЁЈәГчп@Я`ұіҮшғИ(nЁЁi)·ЁкP(guЁЎn)УЪҫҶјsҷа(quЁўn)өДТҺ(guЁ©)¶ЁЈ¬ТІҢўҢ§(dЁЈo)ЦВ—lјsөДҹoР§ЎЈОчІШЧчһйЦРҮшөДТ»ӮҖөШ·ҪРРХю…^(qЁұ)УтІ»ҫЯУР—lјsҫҶјsөДЦчуwЩYёсЎЈыңҝЛсRәйЕcОчІШөШ·ҪҙъұнФЪУў·ҪЛщ”MөДјsёеЙПҶОӘҡәһКрЈ¬ЦРҮшЦРСлХюё®өГөҪПыПўәуЈ¬БоНвҪ»ІҝХХ•юУўК№Ј¬ЦРҮшЦРСлХюё®ҮАХэВ•ГчІ»Н¬ТвәһСәЈ¬ёьІ»ДЬіРХJОҙҪӣ(jЁ©ng)ЦРҮшЦРСлХюё®ңКФSөДУўІШЛщәһ—lјs»тоҗЛЖОД ©ЎЈОчІШЧчһйЦРҮшөДөШ·ҪХюё®ЕcУўҮшәһУҶЯ…Ҫз—lјsЈ¬п@И»Я`·ҙБЛҮшлH№«јsәНГсҮш‘—·ЁөДёщұҫТҺ(guЁ©)¶ЁЈ¬ұШИ»КЗҹoР§өДЈ¬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ТІТтҙЛӣ]УР—lјsөДР§БҰТА“ю(jЁҙ)ЎЈҢҰУЪОчІШөШ·ҪҙъұнЛщЦ^өДәһЧЦЈ¬јУДГҙуҢW(xuЁҰ)ХЯЧT·ёкӮҗ·тФшХJһйЈә“ОчІШөДәһЧЦұҫЙнХэКЗЛьИұ·ҰӘҡБўЩYёсөДТ»ӮҖЦұҪУАэЧCЎЈТтһйОчІШӣ]УР„eөДЯx“сЈ¬Ц»УРН¬ТвУўҮшөДТӘЗуЎЈ”ўЫ
5.—lјsұШнҡЧсКШФӯ„tЎЈ—lјsұШнҡЧсКШКЗТ»ӮҖ№ЕАПөДЎўҫЯУР“ҸҠРР·Ё”РФЩ|(zhЁ¬)өДҮшлHФӯ„tЎЈЯ@ҫНТӘЗуҫҶјs·ҪҢҰ—lјsөДТҺ(guЁ©)¶ЁұШнҡЧсКШЈ¬ұШнҡ°ҙХХ—lјsөДТӘЗуІЙИЎҲМ(zhЁӘ)РРҙлК©Ј¬ВДРРҫҶјs·ҪөДБx„Х(wЁҙ)Ј¬Я@н—Фӯ„tІ»ғHөГөҪҮшлH·ЁҢW(xuЁҰ)јТөДЦ§іЦәНі«Ң§(dЁЈo)Ј¬ТІһйҮшлHЛҫ·ЁҢҚЫ`ЛщХJҝЙЎЈЦРУўЎ¶Аm(xЁҙ)УҶІШУЎ—lјsЎ·ТҺ(guЁ©)¶ЁЈ¬“УўҮшҮшјТФКІ»ХјІўІШҫіЈ¬ј°І»ёЙЙжОчІШТ»ЗРХюЦО”ЎЈ1907ДкУў¶нәһУҶЎ¶ОчІШ…f(xiЁҰ)¶ЁЎ·Ј¬ЖдЦРУР“ұЈЧCіэНЁЯ^ЦРҮшХюё®НвЈ¬І»ЕcОчІШҪ»Йж”Ўў“І»ёЙЙжОчІШЦ®Т»ЗРғИ(nЁЁi)Хю”ј°“ұЈЧCЧрЦШОчІШЦ®оI(lЁ«ng)НБНкХы”өИғИ(nЁЁi)ИЭЎЈўЬУўҮшЕcОчІШөШ·ҪҶОӘҡҫҶјsЈ¬ІўёоХјЦРҮшоI(lЁ«ng)НБЈ¬Я`ұіЖдЛщәһУҶөДҮшлH—lјsЈ¬ТтҙЛХfЈ¬УўҮшХюё®ФЪОчД·Аӯ•юЧhЦРҫҺФмөДЙжј°ЦРҮшОчІШөДёчоҗОДјюҢҰУЪУў¶нлp·ҪХюё®ҒнЦvТІКЗ·З·ЁЕcҹoР§өДЎЈЖдҢҚЈ¬УўҮшХюё®ҢҰУЪ“ОчД·Аӯ—lјs”ј°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өДҹoР§РФТІІўІ»ЦMСФЈ¬ХэИзҝЁ·№ЕЖХЛюЛщЦёіцөДДЗҳУЈә“УўУЎХюё®ЦчТӘТтһйЎ¶Уў¶н…f(xiЁҰ)¶ЁЎ·ЦРөДПЮЦЖРФ—lҝо¶шІ»ХJһйЯ@—lҫҖФЪ·ЁВЙЙПУРР§ЎЈ”ўЭУўУЎХюё®ФЪШҗ –өИИЛРы“PОчД·Аӯ•юЧhһйУўҮш“ЖөҪәЬ¶аәГМҺ•rЈ¬ТІәБІ»БфЗйөШЧIЦSөАЈ¬ДЗР©АыТжЦ»ДЬКЗјҲЙПХ„ұшЈ¬“ОчД·Аӯ—lјs”ӣ]УР«@өГЦРҮшХюё®өДәһЧЦЈ¬ТІОҙұ»¶нҮшХюё®ЛщХJҝЙЈ¬КВҢҚЙПКЗҹoР§өДЎЈ
6.—lјsҫҶҪY(jiЁҰ)ФҪҷа(quЁўn)ҹoКВәуЧ·ХJФӯ„tЎЈҮшлH·ЁТҺ(guЁ©)¶ЁЈ¬Из№ыТ»—lјsһйҹoҫҶјsДЬБҰ»тФҪҷа(quЁўn)өДИЛЛщһйЗТҹoКВәуЧ·ХJЈ¬„tФ“—lјsҹoР§ЎЈўЩУўҮшХюё®ФшУЪ1914Дк7ФВ3ИХјұлҠУЎ¶ИКВ„Х(wЁҙ)ІҝЈ¬УўҮшХюё®І»ДЬКЪҷа(quЁўn)ҶОӘҡЕcОчІШәһЧЦЈ¬“Из№ыЦРҮшҫЬҪ^Ј¬ҫНІ»ТӘН¬ОчІШәһУҶлpЯ…—lјs”ЎЈўЪ7ФВ23ИХЈ¬ФЪПтУЎ¶ИКВ„Х(wЁҙ)ІҝЮD(zhuЁЈn)іКкP(guЁЎn)УЪОчД·Аӯ•юЧhөДЧоәуӮдНьдӣ•rЈ¬УЎ¶ИҝӮ¶Ҫ№ю¶ЁЕъКҫЈәҝј‘]УЎ¶И–|ұұЯ…ҫіҶ–о}І»КЗОчД·Аӯ•юЧhВҡШҹ(zЁҰ)Ј¬ыңҝЛсRәйҫНЯ@·ҪГжМбіцөДУ^ьcәНҪЁЧhЦ»ДЬХJһйКЗЛыұҫИЛөДЈ¬ІўОҙөГөҪУЎ¶ИХюё®өДЕъңКЎЈўЫТАҙЛҝЙТҠЈ¬УўҮшХюё®Іўӣ]УРКЪҷа(quЁўn)ыңҝЛсRәйУ‘Х“ЦРУЎЯ…ҪзҶ–о}ј°УўІШәһјsҶ–о}Ј¬ыңҝЛсRәйі¬ФҪБЛҷа(quЁўn)ПЮЈ¬ТІӣ]УРөГөҪУўҮшЧ·ХJЈ¬ҸДЯ@·ҪГжХf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ТІКЗ·З·ЁөДЎўҹoР§өДЎЈКВҢҚЙПЈ¬УўҮшХюё®іРХJОчД·Аӯ•юЧhӣ]УР®a(chЁЈn)ЙъЦРҮшХюё®ЧчһйҫҶјsТ»·ҪөДИОәО…f(xiЁҰ)¶ЁЎЈўЬ“ОчД·Аӯ•юЧhөДХ„ЕРК§”Ў”Ј¬КЗТтһйУўҮш“Я^УЪһйОчІШ ҺИЎЧоУРАы—lҝо”ЎЈўЭ
ҫCЙПЛщКцЈ¬“ОчД·АӯІЭјs”Еc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І»ҫЯУРәП·ЁРФЈ¬Уў·ҪФЪОчД·Аӯ•юЧhЙПҢҚК©өД·N·NјҝӮzЧоҪKТФК§”Ў¶шёжҪKЎЈЖдәуЈ¬ҹoХ“Уў·ҪУРИОәОТӘЗуЈ¬ГсҮшЦРСлХюё®ҫщҲФіЦЯ@Т»БўҲцЈ¬І»іРХJЛщЦ^“ОчД·АӯІЭјs”Ј»¶ш“ЛщЦ^ыңҝЛсRәйҫҖКЗТ»ӮҖұИОчД·Аӯ—lјsёьуaЕKЎўёьІ»ДЬТҠИЛөД–|ОчЈ¬ХfЛьҢҰЦРҮшХюё®УРјsКшБҰЈ¬ҙ_ҢҚКЗёсНвлxЖжөД”ЎЈўЮЦРҮшҡvҢГХюё®ТІ¶јІ»іРХJ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ЎЈКВҢҚЙПЈ¬УўҮшТІҸДОҙІЙј{ыңҝЛсRәйҢҰЦРУЎЯ…ҪзөДХJ¶ЁЎЈУўУЎХюё®1929Дкіц°жөДЎ¶°¬ЖжЯd—lјsјҜЎ·КХдӣЕcОчІШУРкP(guЁЎn)ЩYБПөДөЪК®ЛДҫнІўОҙҢў“ыңҝЛсRәйҫҖ”ИОәООДјюКХдӣЯMИҘЎЈЦұЦБ1936ДкЗ°Ј¬УўУЎХюё®АLЦЖіц°жөДөШҲDТІТ»ЦұЧсХХӮчҪy(tЁҜng)Б•(xЁӘ)‘TҫҖ„қіцЦРУЎЯ…ҪзЈ¬УўУЎХюё®өДРРХю№ЬЭ ТІҸДОҙФҪЯ^ӮчҪy(tЁҜng)Б•(xЁӘ)‘TҫҖЎЈ
ұҫОДҫҺМ–Јә18875
ЩYБППВЭd
Х“ОД°l(fЁЎ)ұн
ұҫОДжңҪУЈәhttp://www.lk138.cn/shekelunwen/guojiguanxi/18875.html
ЧоҪьёьРВ
ҪМІДҢЈЦш